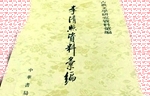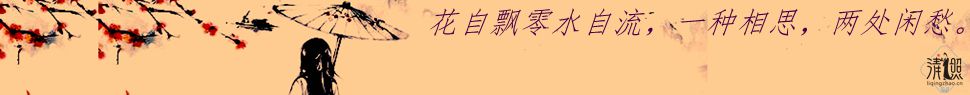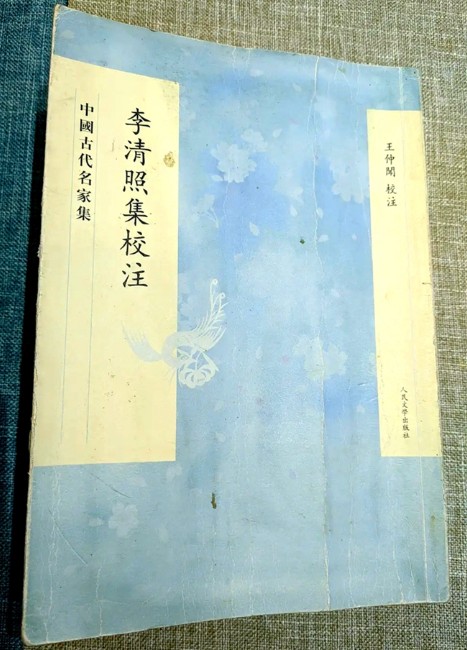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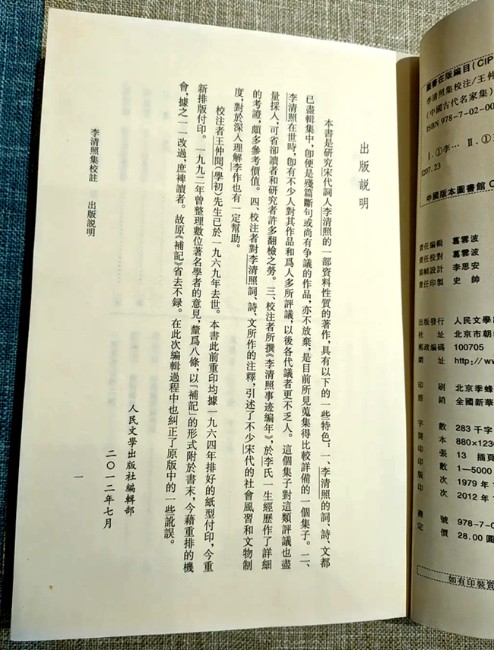
王先生这部书是研究李清照的名著,研究李清照的著述之中,有两类基础性的重大问题是越不过的,一个是李清照词的版本问题,一个是李清照本人的生平事迹。王先生在这两个问题上都穷源溯流,剖析精微,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所谓版本问题,主要是确定一些典籍上记载为李清照写的词是否确为李清照所写,分析众多版本的异同及其可信度。李清照一代大家,在她七十多岁的生涯里流传下来的词作却很少,总共只有四五十首词。同时在前人流传下来的有关词籍著述中,里面收录李清照词的情况又比较复杂,一些词作的作者归属往往似是而非,相互因循,让人莫衷一是,导致后人整理李清照词集的时候多有误收失收之作。
王先生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极为谨慎,他先是网罗众本,把古往今来有关李清照词的著作汇集起来,了解这些书籍中李清照词著录的基本情况,然后凭借他深厚的版本研究功底,分析这些书中关于李清照词叙述的当否得失,最终为我们整理排定出一个最可靠的李清照的著作集,就是这本《李清照集校注》,最终确定可信为李清照所作词43首、调名跟全篇没有保存下来,仅有残句的有两条;存疑之作14首,残句一条,辨明误题为李清照所撰之作29首,误题残句两条。
那么王先生是如何进行版本上的取舍以及断定李清照词的真伪呢?这个可以在他的《全宋词审稿笔记》中可以略窥一二。王先生这部著作是1964年排好纸型的,当时特殊环境下无法出版,直到1979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署名“王学初”。他写这部书的时候应该是他在中华书局编校唐圭璋先生的《全宋词》的同时或稍后。自1960年王先生开始编校《全宋词》开始,历经四年,终于完成,让这部唐圭璋先生汇集有宋一代词作的巨著更加完备和准确。在王先生和唐先生工作往来的《全宋词审稿笔记》中,有着大量的王先生关于词学的精辟论述。根据中华书局出版的影印本《全宋词审稿笔记》第六页开始,王先生与唐先生讨论了编辑全宋词“若干体例上之问题”:
(一)各词来源拟一律以实际见过之书为根据,尊著实据较劣本草堂诗余,而注作洪武本,甚至至正本草堂诗余。因先生引赵万里先生作证,询过赵先生云:绝不应以甲本作为乙本(文字有距离),又如尊稿曾引明钞本惜香乐府,最近亦云:不见得录自明钞本。又如尊稿先引张廷璋藏钞本梦窗词集,而后来则云:原本未见,从朱本抄出。凡此种种俱易造成文字及版本上之混乱与错误。建议凡未实际见过之书或本子,一律不予征引。如有征引必要,一律注明自某某书或某某本子转引(例如毛斧季校乐章集所用宋本柳词集名曰:柳屯田乐章,我们援引时就必须说明从毛斧季校乐章集转引,不要直接引“柳屯田乐章”,免得令人误为此本尚在。又例如明陆正大覆宋晁谦之本花间集,我们如据的双照楼本,就注明双照楼本,不要单称陆正大本,甚至晁谦之本)。
(二)书名人名俱用全称,稿内所称朱本、王本、毛本,拟一律代改作疆村丛书本、四印斋所刻词本、汲古阁本等等,以资醒目,也免得毛校本、毛本纠缠不清;
(三)版本尽量用最早之本或其祖本。上次询问先生改进版本意见,先生认为全宋词所注者不必改动,并以为疆村丛书与所据永乐大典本(四库本)、毛斧季校本等完全相同,不必用其祖本,亦不必再引。试举一例:毛斧季校乐章集,先生曾见过,此次先生且云:疆村源出毛校,何必定用毛校? 疆村本与毛校本基本上相同,但有数字毛校本不误而疆村本误。先生所见毛校本非手校本而为过录本,且或未对勘,故不知毛校本之佳。当然,疆村本集众本之长,用之亦无不可。如能兼用其祖本,岂不更佳?又如明司礼监本草堂诗余出自洪武本,洪武本出自元至正本。赵万里先生云:文字一本不如一本,司礼监本就远不如至正本。书经复刻或传写,总不如原本也。尤其在校改文字时,绝不能用四部备要本、丛书集成本(部分影印本尚可)或舍百衲本二十四史不用而用开明本等等,或不用嘉靖刻顾从敬本类编草堂诗余而用沈际飞本草堂诗余正集或词苑英华本草堂诗余也。
(四)文字必须与所注出处相符。 全宋词稿内常有注出甲书,而实际文字则据乙书,先生云:其本文字不佳故改用他本。文字必须与所注出处相符,否则读者将以为此本文字如此而不知其非(不能要求读者一一检原书自行校勘),文字张冠李戴,不甚妥当。但是,原书如有讹字,仍可进行校改,惟必须注明原作某某,据某某书改作某某。事实上,昔人多如是做(疆村校改各本即是)。校改并非不可,惟须做一交代。(尊稿校改处多未注明,极易造成文字上的混乱。)即有臆改,亦无不可,惟亦须注明原作某某,据文义改作某某,说明编者自改。(先生所改有时很成问题,例如续湘山野录所载苏易简越江吟一首,全宋词稿内先于末句上增加十九字,无任何说明,经指出与续湘山野录文字出入甚大,先生改以上半首从湘山野录,下半首从花草粹编,上云金舆挽,下云金舆转,完全不是原来面目(本来所改已如此,重改后仍如此。)此问题已代为解决。即以湘山野录为正文,另以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六引冷斋夜话又一本文字作注。(全宋词只引花草粹编,实则苕溪渔隐丛话已引有另一本也))
(五)用毛斧季校本即依校本编次及文字。例如陆敕先校毛本珠玉词(尊稿误为毛校本),各首均编有次第数字,文字校改多处,尊稿只用其三处校改之文字,即标曰:毛校本,兹已代按陆校本编次重行黏贴,陆氏校改各字,一律添入,所补各词亦依次编入。毛晋所加之注一律从陆校删去,另以吴讷唐宋名贤百家词本珠玉词校正若干字(一一有注说明),全宋词原误断为苏轼词者,已依宋人旧说断为晏词(宋人据本事曲断为非苏词而为晏词),其他不能下断语者,仅注明别见某某人词集,后记不用,末注:用陆敕先校汲古阁本珠玉词,异文据明吴讷唐宋名贤百家词本珠玉词校改(此本虽有误,胜处殊不少),如先生能据所见之鑑止水斋旧藏明钞本珠玉词与毛刻本互勘作一校记寄下,则晏词文字当更为完善也。(前曾有尊示云“不讲版本”,且校改处已俱有注,自不必另在后记中重复叙述。至于各本优劣,亦涉版本范围,别本误字,尤无胪列或叙述必要。如需详叙,似可另为专著。)毛斧季校乐章集,疆村丛书所刻即依其所标编次,分上、中、下三卷及续添曲子,非仍依汲古阁本编次。
(六)分卷。先生主张不要如毛晋刻词合并卷帙,体例谨严,自很确当。惟全宋词之性质,与宋六十名家词或疆村丛书完全不同,毛、朱所刻,人各成卷,全宋词则不可能如是。疆村分卷,亦不甚安,如刘辰翁词,疆村欲分为三卷而刊版已成,不能改,但目录已明标三卷。以全宋词原稿而论,柳永词原为上、中、下三卷,续添曲子一卷,而稿内则以下卷与续添曲子并为一卷。周邦彦词分为两卷,而所据之四印斋本绝不止两卷也。葛胜仲、叶梦得原可各自成卷,而并为一卷,是全宋词稿已自乱其例矣。拟即全面研究重行分卷,弗使相差过于悬殊。即使原为数卷,并为一卷,似亦无妨。好在原来各卷俱有注明,不至如毛晋所刻之混乱也。
(七)互见词一律注明。全宋词稿内各互见词,有在相关词后注明,有未注,有前有注而互见表内未载,有互见表内有而前完全未注,体例不纯。拟一律注明,以便读者。
(八)互见词一律兼收。现在各互见词,有两处,或三处俱收,亦有只收于一处,体例亦不纯。拟一律兼收,勿有遗漏。
(九)词的编次。一律依所出之书之时代先后为次,同出一书者,以原书中先后为次。全稿各词即依此调整。
(十)人之编次。一律依可知之时代调整,同出一书时代不明者,依原书出现之先后。无名氏作品作为同一作家依上述办法重编。先生所云分组办法,除鼓吹曲外,如全芳备祖,古今合璧事类备要,事林广记,岁时广记合成一卷,标准不很明确,实不知其内在有机联系为何,似可不比分组。
(十一)附录词编次。附录词一卷,混乱异常,拟分为四部分,1、确为宋词而出自小说或伪托神鬼者;2、确为宋词而误题作者姓名者(此大多为互见词);3、出自话本、传奇,号称宋人作品者;4、出自道书之伪词。1、2各依时代编次,3、4依所出之书之时代。
以上办法,是否可行,请提尊见。
李清照画像/图片来源于网络,清照网配图
以上十一条是王先生站在全局角度考虑《全宋词》具体编辑之体例,考虑充分,方法谨严得当,有了这样的通盘考虑,一下子让《全宋词》的编辑有了科学可靠的方法,保证了全书的极高质量。其中第一、第三两条,尤可见王先生考证词集的精审确当。
首先是标举“眼见为实”的原则,引用前人典籍记载一律以实际见过之书,万不得已需要转引的时候,一定要明确转引明细,这样才能保证内容之准确,而不会造成以讹传讹以及文字版本上的混淆。
其次是“版本尽量用最早之本或其祖本”,因为这是可信度最高的版本,价值无可取代。在处理李清照作品版本的时候,王先生虽然罗列众本,但一以时间为序,同一首词是否是李清照所作尽量依据最早之版本,没有这个依据,后世署名为李清照的作品数量虽多,一概存疑或断为他人所作。在这样严谨的态度下,加上王先生涉猎词籍极多,各词籍之优劣异同情形知之甚深,才得以让这部《李清照集校注》既精且全,成为李清照研究方面不得不参考的经典之作,哪怕不看注,只看王先生的“按语”部分,都会获益良多。
当然,学无止境,在版本上精博如王先生,也会因条件限制,有些材料无法见到而有所遗憾。据后来做《李清照集笺注》的徐培均先生所言,有“日本东京大仓文化财团所藏彭氏知圣道斋钞汲古阁未刻词本《漱玉词》,日藏清汪玢辑、劳权手校、道光二十年刊《漱玉词汇钞》(今藏日本东京静嘉堂文库)以及上海图书馆藏清沈瑾钞《漱玉词》(附诗文)一卷”这三种资料,王先生都未能见到,未能用以佐证自己的著述,虽为遗憾,但学问之事每每如是,才见学术之进步也。
关于李清照生平事迹问题,王先生引用大量材料,做《李清照事迹编年》,充分比勘他当时所掌握的文献材料,梳理了李清照一生的行年踪迹。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李清照晚年改嫁张汝舟一事的考订。清照集中有一篇《投翰林学士綦崈礼启》略言其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云钞漫录》等宋人著述中又多有述及,但清代著名学者俞正燮、陆心源、李慈铭、况周颐等人站在自身立场,又对此事持否定态度,影响较大。王先生针对俞、陆、李等人之论述,深入剖析,指出清照晚年改嫁之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云钞漫录》等之记载,确凿无疑,所言有理有据,令人信服。此后学者在这一问题上基本采信王先生的见解而无疑义了。
此外,本书末尾是王先生做的本书《后记》,这是一篇关于李清照的极重要的文章,此文从时代背景、词学演进、李清照词之特点、李清照作品之流传等多方面进行阐述,是一篇增进我们对李清照其人其文的了解的精深之作。读全书之前先读此篇,更能领略书中的妙处。
当然,王先生此书亦非尽善尽美,在李清照词编年方面,在分析阐发李清照词学词艺方面,后人都有更进一步发挥的空间。此外,王先生著此书所用之底本亦未交待(可能是用赵万里先生的宋金元人词辑本),先生言“词、诗依所出之书时代先后为次”,殊觉笼统。
瑕不掩瑜,王先生此书除了精细的考证、深广的见识之外,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就是其中体现出来的王先生治学之门径,沾溉学人,启发后世,这也是王先生流传下来的不多的著述中所共有的特点。王先生的著作与他深厚的学养、精博的学识、真醇的学风一道,永值后人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