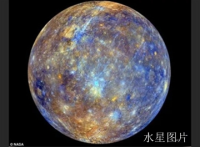我读李清照的《凤凰台上忆吹箫》,奇怪的是,这是一首再明显不过的香词艳曲,一首缠绵委婉的情歌,怎么到了一些评论家的笔下,却变得那么正经。唐圭璋在《唐宋词简释》里说:“此首述别情,哀伤殊甚。......欲说还休,含凄无限。言水念人,情意极厚,余韵隽永。”仅仅是“情意极厚”?历来的正人君子就怕语涉荒唐,总往“琴瑟友好,无邪无妄”上面拉。明代文人李攀龙在他的《草堂诗余隽》中说:“写声声有和鸣之奏。”李清照都怨成这样了,还谈什么和鸣?难道其中的场景一点就不暧昧,当真“被翻红浪”就是“没叠好的锦被象红色的波浪。”那么平常?傻子才相信。

李清照的《凤凰台上忆吹箫》全文是这样的:
香冷金猊,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
任宝奁尘满,日上帘钩。
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
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
休休!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
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
惟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
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
李清照早被千年以来的遗老遗少整得面目全非了。如清代大儒沈曾植在其《菌阁琐谈》说:“易安跌宕昭彰,气度极类少游,刻挚且兼山谷,篇章惜少,不过窥豹一斑,闺房之秀,固文士之豪也。才锋太露,被谤殆亦因此。自明以来,堕情者醉其芬馨,飞想者赏其神骏,易安有灵,后者当许为知己。渔洋称易安、幼安为济南二安,难乎为继,易安为婉约主,幼安为豪放主,此论非明代诸公所及。”此论貌似公允,骨子里还是以正风化。
还是明代人沈际飞《草堂诗余正集》说得痛快:“清风朗月,陡化为楚雨巫云;阿阁洞房,立变为离亭别墅,至文也。”昨夜的欢会只映得眼前的孤单。这才是李清照的真实生活。其实,且不论这“武陵人”是谁?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应该是话灵灵的生命,一个知情知意的女人,非要把李清照诠释的冰清玉洁,忠贞不二,恪守妇道,心如古井,累不累啊。
明明李清照感情丰富,明明李清照词藻绮丽,为什么现存的只有四十多首,而这四十多首词或者苍凉沉郁,或者敦厚教化,就没有一点“色彩”?当真李清照就这么不解风情?李清照的词大都是“怎一个愁字了得”。如果生活美满,琴瑟和鸣,怎么会“人比黄花瘦”;“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再看李清照《怨王孙》中这句“多情自是多沾惹”,那心底的私密,爱意的缱绻虽随着漱玉泉的涓涓细水流逝了,但其深层意蕴是领略不尽的,李清照心中的爱河一定扬起过波澜。
查南宋人王灼作《碧鸡漫志》其中就有涉及李清照这方面的说法:“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妇女,未见如此无顾藉也”。差不多同时代的人讲出这种话,不应该是空穴来风吧。

明代学者杨慎的《词林万选》中曾收录李清照的《丑奴儿》词一首:
晚来一阵风兼雨,洗尽炎光。
理罢笙簧,却对菱花淡淡妆。
绛绡缕薄冰肌莹,雪腻酥香。
笑语檀郎,今夜纱厨枕簟凉。
夏夜清凉,李清照风情无限,和自己心爱的人共浴爱河。
明人陈耀文编写的《续草堂诗馀》中也收了一首李清照的《浪淘沙》:
素约小腰身,不奈伤春。
疏梅影下晚妆新。
袅袅娉娉何样似,一缕轻云。
歌巧动朱唇,字字娇嗔。
桃花深径一通津。
怅望瑶台清夜月,还送归轮。
疏影横斜,李清照绰约动人,一种别样的天真无那。
(这两首词,很多人都认为是伪作,我是宁愿信其有的。)何等绮丽,何等缠绵,何等销魂。女人魅力,精巧心思和充满爱意的感情的无拘束地表露才是真正的李清照,才称得上“中国最美丽的寂寞芳心”。 那些李清照现存的词中的句子:“轻解罗裳,独上兰舟”,“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眼波才动被人猜”,“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才不显得突兀。非要强调“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士大夫气”。岂不知豪情也是情,是情至极处的喷发。没有情辞委婉,那来情辞慷慨?没有儿女情长,绝对没有爱国情深!

据说已皈依空门的燕叟文怀沙曾说:“女人可以略输文采,不可稍逊风骚。”,这句话很有道理。风骚是含蓄优雅,雍容大气,是源于天性本心的流露,所谓“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是也。风骚的女人风姿曼妙,风骚的女人飘逸轻灵,而不是搔首弄姿,卖弄风情。风骚的女人给自己所爱的人是刻骨铭心的记忆。
谁解得李清照婉转愁肠,百千心结?白下烟雨,钟山风云见证了他的孤苦,只不过那呜咽的秦淮河水载不动她无尽的哀愁。我以此文想再现李清照这个女人心中曾有的澎湃,重显本有的幸福,可惜资料太少,也许是枉费心力了。
武陵人远,梦断香消,但愿沉淀了千年寂寞的李清照能回眸一笑。
导读:“此首述别情,哀伤殊甚。......欲说还休,含凄无限。言水念人,情意极厚,余韵隽永。”仅仅是“情意极厚”?历来的正人君子就怕语涉荒唐,总往“琴瑟友好,无邪无妄”上面拉。
责任编辑:文浩
特别声明:文章凡没有注明“来源:清照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他网络媒体,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文化传播。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清照网观点或立场。如有关于作品内容、版权或其它问题请于作品发表后的30日内与清照网联系。
相关阅读

李清照
李清照(1084年3月13日—约1155年),号易安居士,汉族,齐州济南(今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人。宋代女词人,婉约词派代表,独树一帜,人称“易安体”。有“词国皇后”、“一代词宗”、“千古第一才女”之称。
李清照出生于书香门第,早期生活优裕,其父李格非为北宋著名文学家,藏书甚富。李清照自幼秉承家学,博览群书。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嫁于吏部侍郎赵挺之第三子赵明诚。婚后夫妻二人琴瑟和弦,一生致力于书画金石,共同完成《金石录》30卷。
“靖康之变”(1127年)北宋朝廷崩溃。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夫赵明诚病逝于建康(今南京)。李清照流寓南方,境遇孤苦。著有《词论》一文,提出词“别是一家”。能诗文,感时咏史,抒发爱国情怀。《宋史·艺文志》载有《易安居士文集》7卷、《易安词》6卷,已散佚。后人有《漱玉词》辑本。今有《李清照集校注》。
推荐
- 浅析李清照诗词中的爱国情怀
- 李清照的《咏史》“两汉本继绍,新室如赘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详情
- 纪念李清照诞辰936周年
- 1084年3月13日杰出女词人李清照出生,自此之后中国词坛上多了...详情
- 李清照是个“酒色之徒”吗?
- 人们通常将其视为文学史上最著名的甚至是唯一可以与男性大词人相匹配...详情
- 南京“古琴书画家”张正吟:拒伪政权自沉相抗
- 张老省吃俭用,曾先后珍藏了二十多张古琴,多为南宋、明、清艺人的佳...详情
- “千古第一才女”李清照:谁说女子不如男?
- 宋代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尤其是词在宋代达到了全盛,后人...详情
- 李清照——一个雌雄同体的女汉子
- 中国几千年文学史上,试问谁为千古第才女,李清照当之无愧。在理学当...详情
热点
-
- 李清照环形山——“千古第一才女”,水星上镶嵌着您的名字
- 1976年,国际天文学会聘请一些专家、学者为环形山命名,1987...
-
- 李清照的弟弟是谁?姐弟俩有什么交往?李清照晚年遭遇如何?
- 据李清照诗歌记载,她有一个弟弟叫李迒。靖康灾后,李清照和丈夫赵明...
-
- 年少不懂李清照,读懂已是伤心人
- 《宋史》说:“拱辰孙女,亦善文。”父母都喜欢大唐诗人王维的诗,尤...
-
- 文化名人专题之走近李清照
- 文学史上的李清照,一生都从事学术的研究与文学之创作,读她的「金石...
-
- 泼茶香:李清照的“当时只道是寻常”
- 故事就从清朝词人纳兰性德的一首词开始。词曰: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
-
- 历史第一女词人李清照,多愁善感却从不柔弱
- 她是历史第一女词人,写出了"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帘卷西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