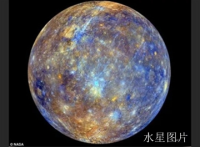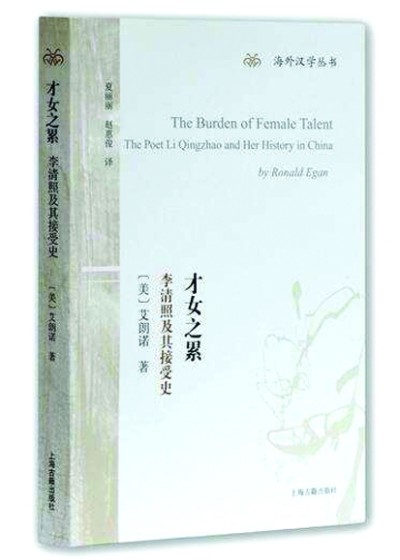
《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
[美]艾朗诺著 夏丽丽 赵惠俊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成玮
提到女词人,第一个想起的,自然是李清照。作为中国古代唯一跻身一流作家行列的女性,生前身后,她都相当引人注目。然而存世作品无多,生平资料寥寥,与其巨大的声名,形成一种反差;加以名满天下,谤亦随之,毁誉纷纭,更使其形象扑朔迷离。历经近千年探讨,李清照生平与创作的诸多问题,似乎有了定论,可必须承认,某些结论,依据未必坚实。艾朗诺先生著《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对此展开系统反思,尝试提出一家之言,是晚近李清照研究的一大收获。
如书名所示,该著同时在两方向用力:梳理李清照的接受史,还原李清照的本来面目。在某种程度上,前者构成后者的出发点:正因为剥落了接受过程中的种种涂饰、扭曲,寻绎原貌方成为可能。
就作品接受而言,李清照在世时,诗词文便颇受赞誉。晚明以降,女性写作盛行,词体复兴,这两项原因促使论者将她塑造为前代的女词人典范,其声望因而更上层楼,牢固树立起来。就生平接受而言,李清照的问题,是在赵明诚殁后改嫁张汝舟。这在当日原无不可,但随着南宋后期以来,理学家对于夫死守节的大力倡导;元代以来,朝廷法令的推波助澜,再嫁逐渐变成一件不名誉的事。既是备受推崇的才女,又是妇德有亏的妻子,褒贬左右为难。为摆脱这一困境,自清代起,掀起一场替李清照“辩诬”的运动,否认她曾再婚。直至1957年,黄盛璋再度提出改嫁说。迭经争论,进入二十一世纪,学界才“基本上接受了再嫁这一事实”。此前关于李清照接受史,不乏研究成果,著者未满足于就事论事,而自南宋以下的观念与社会背景入手,解释李清照形象的演变轨迹,深度遂远迈以往。
面对李清照的诗文与词作,本书采取截然相反的解读策略:一方面,努力把诗文置入其生平脉络,审视具体语境,推求纸背深意;另一方面,又努力把词作与生平隔断,限就作品本身立论。在著者看来,易安诗风格与题材的“男性化”、《词论》所探索的全新词体观、《打马图经序》与《打马赋》的政治及军事指涉,皆系一位女作家抵抗男权社会歧视,捍卫创作权利,“以刚克刚”的奋斗。李清照性格伉爽,不类寻常女子,前人早已言及。缪钺先生即称她“有胆、有识、有魄力,独能冲破封建藩篱,以一弱女子而关心国家大事,纵论文学,臧否人物,发抒己见,无所顾忌,这是很难能而可贵的”(《灵谿词说·论李清照词》),论据也约略相近。本书借鉴女性主义视角,不惟赏其性格,抑且探其心曲,将这些表现归因于男权社会施加的精神压力,所论更透入一层。《金石录后序》自述同赵明诚的婚姻与收藏生活,娓娓动人。著者却注意到,这篇文字写于李清照再婚张汝舟又迅即离异之后,由此专辟一章,抉发字面下的隐秘动机:赢取世人同情,保护剩余文物;提醒读者不可把文中所述当成事实,无条件接受下来。此文复杂面向,宇文所安已有所察觉(《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不过他只细绎文本,未及联系作者经历。本书知人论世,思考更为全面,故而又读出不少新见。

李清照主要以词名家,本书最关键的创获,也在这一方面。易安词集久佚,南宋文献里仅存三十六首,其余均见于元以后文献。从流传有绪的角度考虑,著者只认南宋所见之作为真,就中复去除疑点重重的黄大舆编《梅苑》所收六首,凡得三十首,此外一概存疑。李清照词历来有真伪之辨,本书标准大约最是严苛。至于词作内容,以女性生活与爱情为主体,论者一向多从作家生平求解,著者却指出,主流读法值得商榷。词在当时,多数情形下属代言体,易安词也不例外,篇中女性难以遽目为作家本人。这一观点极具开创性。各家自传式解说,先撷取词里若干生活印象,譬如夫妻久别,而后证诸生平。每逢书阙有间,便“用最琐碎的线索,做最大胆的推断”,曲折以赴之。纵如此,推演的景象仍不能尽符词作所言,跋前踬后,摇摇欲坠。而一旦破除既有思维定势,视词为代言体,与李清照的生平分离,所有窒碍顷刻迎刃而解。女词人在作品中不是女词人,这个创见的价值即在于此。
本书思路整体观之,或承继旧说而力破余地,或独辟蹊径而益趋合理,在每一方向皆有开拓,诚属难得。落实到具体论断层面,则不无可商之处。譬如著者认为,清人辩称李清照未尝再婚,背景在女性守节的严格化,大体可从。麻烦出在,第一位广罗文献论证此说的俞正燮,恰是思想开明,主张“其再嫁者不当非之”(《节妇说》)的。其《易安居士事辑》明言:“是非天下之公,非望易安以不嫁也。不甘小人言语,使才人下配驵侩,故以年分考之。”他反对再嫁论,与其说出于贞节立场,毋宁说出于对结缡双方雅俗悬殊的惋惜。本书力求把一切“辩诬”者,纳入单一背景之下,对此文的阐释,遂未免失之迂曲。又如考察易安诗文,不仅诠释方式迥异于词,真伪判断也大相径庭。对词严加甄辨,对诗文则全盘接受,绝无疑议。实则诗文和词一样,均系后人辑得。其间有无赝品,字句有无窜易,并非不言自明。举《词论》为例,早在1980年代,马兴荣先生已质疑其著作权(《李清照〈词论〉考》),至今尘埃未定;或又谓此篇“在传闻过程中字句原意难免改动失真”(孙望、常国武主编《宋代文学史》)。倘与词作一视同仁,似也应下一番考辨工夫,而非不假思索,坦然据以为说。再如代言体之论,固然极富意义,但是,著者太珍视自己的新解,倾向于把易安词统一划归代言体。即便发现“李清照甚至允许在词中时不时地出现与她生平有关系的细节”,依然强调,这类作品“还是必须和李清照本人相区分开来”。如是处置,恐怕难餍人意。以常理度之,易安词一部分系代言,一部分系自传,两者兼有,方为正常状态,无须偏取一端。展望未来,在可能范围内,尽量辨明多少词作属于前者,多少词作属于后者,或将变为讨论李清照的一项新议题。
昔日郑昕《康德学述》弁言有云:“超过康德,可能有新哲学;掠过康德,只能有坏哲学。”本书一些具体论断,终究会被“超过”,这也是学术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然其思路多有创新,示来者以轨辙,却不容“掠过”。仅此一点,足以保证它在李清照研究史上,占据无可替代的一席之地。
导读:作为中国古代唯一跻身一流作家行列的女性,生前身后,都相当引人注目。然而存世作品无多,生平资料寥寥,与其巨大的声名,形成一种反差;毁誉纷纭,更使其形象扑朔迷离。
责任编辑:文浩
特别声明:文章凡没有注明“来源:清照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他网络媒体,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文化传播。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清照网观点或立场。如有关于作品内容、版权或其它问题请于作品发表后的30日内与清照网联系。
相关阅读

李清照
李清照(1084年3月13日—约1155年),号易安居士,汉族,齐州济南(今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人。宋代女词人,婉约词派代表,独树一帜,人称“易安体”。有“词国皇后”、“一代词宗”、“千古第一才女”之称。
李清照出生于书香门第,早期生活优裕,其父李格非为北宋著名文学家,藏书甚富。李清照自幼秉承家学,博览群书。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嫁于吏部侍郎赵挺之第三子赵明诚。婚后夫妻二人琴瑟和弦,一生致力于书画金石,共同完成《金石录》30卷。
“靖康之变”(1127年)北宋朝廷崩溃。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夫赵明诚病逝于建康(今南京)。李清照流寓南方,境遇孤苦。著有《词论》一文,提出词“别是一家”。能诗文,感时咏史,抒发爱国情怀。《宋史·艺文志》载有《易安居士文集》7卷、《易安词》6卷,已散佚。后人有《漱玉词》辑本。今有《李清照集校注》。
推荐
- 纪念李清照诞辰936周年
- 1084年3月13日杰出女词人李清照出生,自此之后中国词坛上多了...详情
- 李清照环形山——“千古第一才女”,水星上镶嵌着您的名字
- 1976年,国际天文学会聘请一些专家、学者为环形山命名,1987...详情
热点
-
- 李清照环形山——“千古第一才女”,水星上镶嵌着您的名字
- 1976年,国际天文学会聘请一些专家、学者为环形山命名,1987...
-
- 纪念李清照诞辰936周年
- 1084年3月13日杰出女词人李清照出生,自此之后中国词坛上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