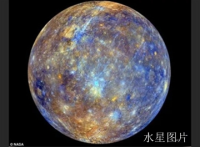接受之累
男性作家和评论者赏识李清照的词,却不能回避她的晚节是非问题。如此,则“作为女性作家典范”的李清照与“没有操守”的李清照之间的矛盾就愈加尖锐(艾著323页),也就有了后人对李氏其人其事及其作品接受时出现的两难选择。
对其词作的接受,主要是指对李清照小词的解读。艾著认为现存最大的弊端,就是自传性的解读。长期以来,这些传统的解读,仿佛认定李氏词只能被理解为简单的第一人称叙述,只是反映了词人的私人情境(艾著169页)。因李清照词真伪杂陈,解读中就会出现以下现象:一旦被认为是原作,就会被套用李氏生平,很可能被系年,用来重构词人的身世(艾著87页);一旦被鉴定是李氏的作品,就不会被视为平庸;一旦被署上李氏的名姓,疑作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原先的陈词滥调也被注入了新的光彩和感召力。凡此种种,是以伪历史或传记体的阅读方式来理解作品,把李氏词看成字里行间都充盈着词人自己的所思所感(艾著308页)。更有甚者,词人的身世也可能被相应地篡改,而且这类“修改”在李清照身上并不少见(艾著314页)。这种现象的确存在于对古人作品的解读与研究中,其中或有出于标新立异等目的而强作解人。

对其形象的接受,则由于李清照生平资料罕见,其作品反而促成了其形象的形成。艾著认为这一形象的生命和推动力却是男性读者和评论家所赋予的,并将之复杂化、浪漫化,其原因在于这一形象投合了男性的审美观,他们通过编选李氏的作品使其强化。此外,男性文人还把这个形象编入了小说轶闻,使其更加复杂精细。李清照本人促成了这个形象,但是最终的复杂与夸大版本,却是在历史的长河中,被与她毫不相关的人创造和定型的,这远非词人自己所能掌控,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李氏的全集在南宋选家重建自己心中的词人形象之后可能就散佚了,于是选家们建构出的李氏形象,实际上有着特别的影响力(艾著182页)。李清照在南宋时被视为晚节有失,历元明清以至近现代,在学者中就出现了承认与否定的两种态度,在否定一方成为主流观点时,要把李清照这样的女子纳入男性文人圈,就得对之美化与净化,必须对她的形象及其立场以微妙或不怎么微妙的方式加以改变,就会有重塑李氏形象的事发生,如晚清方志中,李清照传从“文苑”移至“列女”(艾著226页),“列女”部分记载当地的女性道德英雄,李清照的形象显然就是被改造过的形象。
不论是小词的解读,还是形象的重塑,艾著指出了对李清照其人其文的研究与解读中存在的种种不是,并提出了不少富有建设性的看法。

艾著在研究李清照中,引入女性主义,借此提供一种全新的视角和理论基础,来挑战李清照的传统解读模式,针对老问题提出新方法,促使人们反思其人其文,使这部著作充满亮点。由于李清照的生平资料匮乏,存在着对前人的记载又有不能坐实的困惑,其中存在着的矛盾心理是难以消除的。元人陈世隆《宋诗拾遗》卷十一云:“李格非,字文叔,济南人,自号易安居士。”知李格非也号易安,而李清照为格非女。陈世隆,字彦高,书前陈氏小传云:“诗文集不传,惟《宋诗补遗》八卷,《北轩笔记》一卷,彦博馆主人陶氏有其抄本云。”今存有《两宋名贤小集》,为抄本,题陈思辑,陈世隆补,此书荟萃两宋诗人小集二百四十种,《宋诗拾遗》或针对此书而言,《宋诗补遗》或即《宋诗拾遗》,只是卷数不同,当是传抄歧岀。《宋诗拾遗》藏南京图书馆,为旧抄本,凡二十三卷,为海内孤本。收两宋诗人近八百,诗一千四百多首,其中不少诗作仅见于此书,一些小传中有关作家的行迹,也为他书所不载,文献价值颇高。其云李格非号易安居士,当有其资料来源。易安之号本于室斋名(如李清照《上枢密韩肖胄诗》《打马图序》《金石录后序》等文均有易安室之称),这个室斋名疑最初为李格非所用,后为其女李清照沿用,并作为自己的别号。如果李格非确实曾号易安居士,那么署名李易安的部分小词以及《词论》作者等的归属就成了问题,解读的困惑仍会继续,当然这并不妨碍李清照成为才女的事实。
(作者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