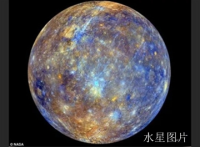李清照作为千古第一才女,诗大气纵横,词婉约精奇。
而她的人生和诗词风格以赵宋王朝南逃作为分界点,前半生语言清新自然,欢快美满,偶有闲愁点缀;靖康之变后伴随着生活的颠沛流离,主要书写苍凉人生,抒发对故乡故国的怀念。
而《词论》作于南渡前,这一时期,李清照自身文学风格虽没有大的感情波动,但是已经日趋成熟,对词作有了比较完整的、成熟的看法。除了和她同期的宋词三巨头之一的周邦彦之外,她将她前面的词人评了个遍。谈宋词却不谈周邦彦,是没有道理的事情。
这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当世不论”,另一个是李清照夫家与周邦彦政治上的不合,导致《词论》没有讨论周邦彦的作品,实际上把掌管“大晟府”的“词中老杜”周清真排除在外,整个《词论》的格局是差了一点的。
李清照确实是对欧阳修、苏轼、柳永做出了批评。不单只这几位名家,基本上没有词人躲开了她的批评。由于李清照本身的词风走的晏欧派,缺乏眼光向外的视野,对苏轼等人在词史上的作用不像我们后来人的上帝视角看得清楚,所以也有一些局限性。所以有人说她:“多有妄评诸公……”

以上按下不表,我们只看她是如何批评欧阳修、苏轼、柳永的。
她的《词论》是按时间先后对诸位词人发表评论的,那么北宋初第一位重要词人自然是“奉旨填词柳三变”了。
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
这里指出了柳永于宋词的最大成就,“变旧声作新声”,实际上就是指柳永对原来的小令格式的词牌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充,为后来周邦彦长调的确立做出了开创性的奠基。同时指出柳永的词大行于世,而柳永作为一个会作词的音乐家,他的作品是非常合音律的,但是由于他作品的花街柳巷的属性,“词语尘下”——作品格调不高。
其实格调不高并不单是柳永的词,词作为“诗余”,初期本身的功用就区别于诗的高大上,在市井中盛行,是无法写得太高雅,否则如何能做到“凡有井水处,便能歌柳词”?
而柳永如今流传于世的大都是干净、婉转、悲切的词作,比如大家都熟悉的《雨铃霖》之类的,只是作为整体来说,他的词多为生活所迫而写,流转于娼门酒肆,难免“词语尘下”。

而欧阳修、苏轼在《词论》中,李清照是一同评论的:
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何耶?
晏元献,就是晏殊。欧阳永叔,就是欧阳修。苏子瞻,就是苏轼。
这里首先肯定这几位大家的学问:“学际天人”,天道人道的学问他们都通晓,意思是无所不知,而用这学问来写词,那简直就是往大海里面倾倒一瓢水而已,“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简直就是大材小用,轻松写意。
但是——世间事就怕但是,“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但他们的词作都只能算是句读不整齐的诗罢了。“句读”,就是断句,句读不葺之诗,就是长短句。
李清照为什么这么说晏殊、欧阳修、苏轼呢?
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晏、欧阳、苏这三位大家实际上走的就是词的去音乐化的路子。由于一些古乐的渐渐散佚,很多词牌逐渐独立于音乐之外而存在,慢慢地只靠汉字本身的平仄音调来树立作品的音律。这其实是走的诗在汉初一样的路子。

又往往不协音律,何耶?
而这种不再看重音律,只看重词牌本身音韵的作品,在当时不是主流。当时什么是主流?周邦彦的“大晟府”钦定各种音乐词牌规范。李清照作为当世词人,必然深受周邦彦影响,而且她自身的观点也是如此,整个时代的观念都是如此。一,词牌必须附着于音乐存在。二,词牌就该婉约。
当时苏轼的豪放派尚未完全成型,叶梦得,张元干,辛弃疾还是后来人。李清照面对的最大问题是晏、欧阳、苏的词牌去音乐化。所以李清照的批评重点也就放在这个上面。
在李清照看来,“词别是一家。”
我们也要看到,在古乐尽失的今天,这已经不是个问题。我们如今区分词牌的流派,是从内容上来区分,已经完全与音乐无关。而实际上,晏殊、欧阳修的词是南唐闲相冯延巳的风格,在宋词中我们称为“晏欧派”,这与柳永的“婉约派”,苏轼的“豪放派”完全都不是一个路子。
李清照当时看到的只是词牌去音乐化的这种危险走向,所以,她写《词论》的时候把“晏欧派”和“豪放派”放在一起给批评了。

而实际上,我们今天归类,李清照和秦观一样,本身就是晏欧派的传人。
把晏欧派和豪放派并论,是李清照处于当时代的局限性,她没看到苏轼对词牌内容的开拓的意义远大于晏欧派和柳永在格式上的突破。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因身在此山中。
导读:李清照作为千古第一才女,诗大气纵横,词婉约精奇。而她的人生和诗词风格以赵宋王朝南逃作为分界点,前半生语言清新自然,欢快美满,偶有闲愁点缀;靖康之变后伴随着生活的颠沛流离,主要书写苍凉人生,抒发对故乡故国的怀念。
责任编辑:王艺轩
特别声明:文章凡没有注明“来源:清照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他网络媒体,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文化传播。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清照网观点或立场。如有关于作品内容、版权或其它问题请于作品发表后的30日内与清照网联系。
相关阅读

李清照
李清照(1084年3月13日—约1155年),号易安居士,汉族,齐州济南(今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人。宋代女词人,婉约词派代表,独树一帜,人称“易安体”。有“词国皇后”、“一代词宗”、“千古第一才女”之称。
李清照出生于书香门第,早期生活优裕,其父李格非为北宋著名文学家,藏书甚富。李清照自幼秉承家学,博览群书。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嫁于吏部侍郎赵挺之第三子赵明诚。婚后夫妻二人琴瑟和弦,一生致力于书画金石,共同完成《金石录》30卷。
“靖康之变”(1127年)北宋朝廷崩溃。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夫赵明诚病逝于建康(今南京)。李清照流寓南方,境遇孤苦。著有《词论》一文,提出词“别是一家”。能诗文,感时咏史,抒发爱国情怀。《宋史·艺文志》载有《易安居士文集》7卷、《易安词》6卷,已散佚。后人有《漱玉词》辑本。今有《李清照集校注》。
推荐
- 纪念李清照诞辰936周年
- 1084年3月13日杰出女词人李清照出生,自此之后中国词坛上多了...详情
- 李清照环形山——“千古第一才女”,水星上镶嵌着您的名字
- 1976年,国际天文学会聘请一些专家、学者为环形山命名,1987...详情
热点
-
- 李清照环形山——“千古第一才女”,水星上镶嵌着您的名字
- 1976年,国际天文学会聘请一些专家、学者为环形山命名,1987...
-
- 纪念李清照诞辰936周年
- 1084年3月13日杰出女词人李清照出生,自此之后中国词坛上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