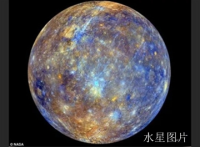李清照是谁?

在当下中国,谁敢问这个,必然引来哄堂大笑。因为大家都“知道”,李清照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诗人,似乎人人谁都能背出几首她的“代表作”。
然而,我们是如何“知道”的呢?如果没有学校教育,我们还能“知道”吗?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教育通过近似的课本、雷同的讲授方式、标准化试题等,虚拟出一种“剧场效应”——我们俨然生活在同一氛围中,正经历着同一历史——其中的重要性、前后顺序、发展规则等均已预设,只有坚信这些是“真实的”,我们才能通过一次次考试,拿到毕业证书。
这是一个巨大的虚拟游戏,答对一次,便能获取一次奖励,而答错一次,就要接受一次惩罚。如此反复规训,则李清照内化为常识的一个组成部分,谁敢质疑,立刻会有旁人站出来加以痛斥。
然而,在李清照的形象中,始终存在着两个巨大的疑问:
首先,李清照的文坛地位太独特。据梅维恒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统计,“公元一世纪开始,两千年中华大地上一共出现二十九位著名女作家”,这些“著名女作家”多是业余作家(很多人本业为妓女),她们的少数作品之所以能留下来,仅为“聊备一格”,只有李清照的作品实现了经典化,为后人所师法。
其次,李清照的大多数作品真伪难断。据饶宗颐先生说,可确认为真的不过20多首,但李的诗集在清代便已达80多首,加上1949年后的“新发现”,如今已突破百首。换言之,我们脑海中的“名句”很可能是赝品。其实,就算是真品,今人理解与李清照的创作本意之间,也会有巨大差别,可这却不妨碍人们宣称:我与李清照心意相通。
显然,这两个BUG是经典化过程中的残留物。因为经典化不是一个完全客观的、自然的过程,作品好,未必就能成为经典,经典与否,关键看人怎样去塑造它。

为了不朽,李清照够拼
众所周知,李清照的词独树一帜,这是因为词多在宴饮时由歌妓唱出,作者往往要模拟歌妓的口吻,而当时男性作家对女性心态了解不多,容易走向肤浅。李清照则不同,她本身就是女性,冲口而出即可,故有自然之美。可以说,正是词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赋予李清照艺术生命。
李清照对此有异常清醒的认识,为实现经典化,她采取了主动出击的策略,即:强调词的独特性,刻意与诗相区别。
在《词论》中,李清照对当时名家多有贬斥。她批评晏殊、欧阳修和苏东坡:“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批评曾巩、王安石的词“人必绝倒,不可读也”。以此提出“词别是一家”的主张。
严格来说,《词论》是用两把板斧砍人。对苏东坡、王安石等人的创作,李清照认为韵律太差,可对柳永等人的创作,李清照又认为“词语尘下”。一会儿重形式,一会儿重内容,让人难以适从,是用否定来完成建构。
建构“词别是一家”,还有一层意义,即:避免了与历代伟大诗人直接对比,凸显了自己创作的价值。
其实,李清照也曾试图融入到诗的传统中,如“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堪称“不平则鸣”,可在传统时代,女性作家生活空间相对狭窄,“文以载道”绝非她的擅场。但李清照因地制宜,将个体命运与家国天下联系起来。这体现在《金石录后序》中,它将美好追忆、现实伤感与人生渴望三种情感,编织到金灭北宋的历史大背景中。
李清照写《金石录后序》,很可能是在经历了失败的再婚后,为重新获取皇家遗眷(她的前夫赵明诚为皇族后裔)身份而进行的一次努力,以她多年积累的文字修为,她不仅实现了功利目的(得到宋高宗赵构认可),还顺手创造了中国散文史上一个独特的、感人至深的写作风格。
明朝人为何重新发现李清照
然而,只靠个人努力是不足以完成经典化的。
李清照父亲李格非是“苏门后四学士”之一,文坛地位崇高,当时文人均愿给她一点褒扬,但李清照生前出了两本诗集,均很快失传。
南宋评论者承认李创作有特色,但认为她的作品中过分透露了闺门中事(相关作品似乎都已失传,如今留下的李清照的一些艳词可能是后人伪作)。直到元代,文坛领袖杨维桢仍认为李清照“出于小听挟慧,拘于气习之陋,而未适乎情性”。
明中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发达,江南出现了闺塾师这一职业,富商家的女孩得以接受良好教育,能文善诗者渐多,她们组成诗社,甚至将相关作品结集出版。面对充满性别歧视的主流文化(直到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中,林黛玉仍认为出版闺阁诗是浮浪之举),女作家们要为自身行为寻找合法性,就必须寻找历史证据,以表明“从来如此”,她们的努力得到许多文人的支持。在此背景下,李清照被“重新发现”。为不使李孤单,明代文人们还塑造出了朱淑真。与李清照不同,朱淑真很可能是虚构出来的。在传说中,朱的出生时间有多个版本,前后相差竟达两百年。有了朱淑真,李清照就有了可应和酬唱的伙伴,则明代女性也可坦然组织诗社了。

后人不批准李清照再婚
在李清照的“再发现”中,暗藏着一个风险,即她曾再婚。
在宋代,女性再婚虽受市井议论指摘,但在具体实践中并不罕见,因宋代法律承认女性私有财产,嫁妆归女性所有。元代时,草原民族法律进入中原,游牧生活不易贮财,故嫁妆归夫家所有,有了经济理性的制约,女性再婚渐成畏途。明代初期兴起“去元化”运动,朝廷广立贞节牌坊,故明清两代,女性再婚为流俗所不容。当李清照成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反面典型时,显然不宜将她树为榜样。
然而,系统是活的,有怎样的漏洞,就会有怎样的补丁。
晚明文人徐公式在《徐氏笔精》中首次提出:“作序(指李清照名作《金石录后序》)在绍兴二年(1132年),李(李清照)五十有二,老矣……必无更嫁之理。”“更嫁之说,不知起于何人,太诬贤媛也。”
徐公式之说并无多少历史依据,在宋代笔记中,关于李清照再婚的记录比比皆是,李清照在个人书信中也坦承此事,可经清代卢见曾、俞正燮、李慈铭等著名学者“论证”后,“李清照未再婚说”反而成了主流。
清末民初,随着日本人编纂的《中国文学史》传入,中国学者倍感压力,救亡图存成了文学史写作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与西方文学史中女性写作传统相抗衡,李清照再被委以重任,成为民族国家建构中的基石。
从闺阁诗人成为经典诗人,进而成为“女中丈夫”,这使关于李清照婚姻生活的讨论一度变成禁区。
真正的李清照更加丰富
随着经典化,李清照的诗集正变得越来越厚,反而因此陷入逻辑悖论中:混入伪作太多,以至于我们很难了解李清照的真实写作风格,信息增加了,她反而被淹没、被抹去了。
从根本上说,经典化是反个性的,它不承认偶然、随意和自由。
欧阳修、晏殊等儒家学者写过大量艳情诗,很少有人据此认为他们行为不检点(也有评论者说那些是伪作),可李清照却没有这种自由。只要流露了离别的悲伤,那就必然是晚期作品,只要写了爱情的甜美,那一定是早期创作。
诗歌创作与事实之间真是一一对照的关系吗?作家难道只是现实的被动反应者?可现实是,李清照的人生履历已成后人鉴定真伪的“依据”,真伪之辨,全看能否契合到她的履历中。
总之,李清照不能偶尔淘气一下,不能清醒时写“浓睡不消残酒”,不能在陆地上想到“争渡”,如果她没看见“鸥鹭”,她就永远也不会碰那两个字……她的一切作品必须是为苍生请命,是歌颂祖国大好河山,她从没想过争文坛地位,从没不着痕迹地抄袭过别人,可世上真有这样的完人吗?
顾颉刚先生曾说:历史是层积的,时间越久,层积的就越厚,就越难理清真相。而李清照的形象变迁史,恰好印证了顾先生的睿见。这也提醒我们,许多被确信的东西未必就是事实,在未经一番知识考古前,我们应保持起码的审慎。
对许多中国读者而言,接受史研究是一个陌生的领域,但只有站在这片高地上,我们才能明白:我们所熟悉的李清照其实是人工制造出来的,真正的李清照远比它丰富。(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