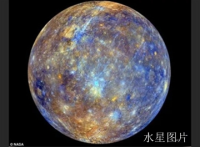张琰在为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作的序中说:“文叔(李格非字)在元祐官太学。丁建中靖国(亦为徽宗年号)再用邪朋,窜为党人(省略主语,意为李格非被窜改成元祐党人)。女适赵相之子,亦能诗,上赵相救其父云:‘何况人间父子情’。识者哀之(看到的人为她感到哀伤)。”

张琰录的只是李清照给公公信中的其中一句,以李清照的文才,那信当是写得极为感人,所以才会“识者哀之”。但公公赵挺之并没有帮忙,或许他也确实没法施以援手。当时,朝野上下对元祐党人避之不及,谁敢替被列入元祐碑中的人说话?何况赵挺之还与元祐党人有一些瓜葛。然而,在李清照看来,公公置儿女亲家于不顾,是冷酷无情的铁石心肠。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载:“李氏格非之女,先嫁赵诚之(赵诚之系笔误,即指赵明诚。先嫁之语意为有再嫁之事),有才藻名。其舅正夫(正夫为赵挺之字,古文中舅姑亦指公婆)相徽宗朝(在徽宗时当宰相),李氏(指李清照)尝献诗曰:‘炙手可热心可寒?’”晁公武录的是其中一句,但就是这一句,李清照的愤怒和不逊已跃然纸上。
不知道赵明诚知道李清照给他父亲呈了这样的诗后怎么想,但从夫妻俩并没有因此反目这点来看,赵明诚对父亲在这件事上的无动于衷是心存芥蒂的,至少对李清照的“忤逆”表示理解和谅解。不知道赵挺之看了这诗后怎么想,是怒火中烧气不打一处来,恨不得把这自恃会填几阕词吟几句诗,就把什么都不放在眼里,连公公都敢讽刺的儿媳赶出赵家?还是宰相肚里能撑船,把这看成是不到二十岁的小女子在发脾气使性子?也许,为官多年的赵挺之在读了李清照的诗后,觉得还真让似乎涉世未深的儿媳给说对了,别看今天炙手可热,对明天心里还真捏着一把冷汗呢!
崇宁四年(1105年),当了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不久的赵挺之,因与蔡京矛盾加深,只好称病辞了职位。《宋史·赵挺之传》载:“(赵)与京争位,屡陈其奸恶,且请去位避之。”到了崇宁五年,蔡京罢相,赵挺之东山再起官复原职。
据说宋徽宗用情专一,为政却朝令夕改,就像他不断改换年号一样,朝廷的官员也是轮番罢黜。时隔一年的大观元年(1107年),蔡京又复相位。这次蔡京抓住赵挺之为官是元祐时期宰相刘挚推荐的把柄,说赵挺之包庇元祐党人。于是,赵挺之又一次被罢官。再也经不起折腾的赵挺之回家五天后在愤懑悔恨中去世了。赵挺之的赠官被朝廷收回,其子的荫封也随之失去。再也无法在京城立足的赵明诚只好带着李清照去了老家青州,直到十年后被重新起用。
对于那段日子时局变幻造成的悲欢离合,李清照曾借咏七夕写过一首《行香子》:“草际鸣蛩,惊落梧桐,正人间天上愁浓。云阶月地,关锁千重。纵浮槎来、浮槎去,不相逢。星桥鹊驾,经年才见,想离情别恨难穷。牵牛织女,莫是离中。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
李清照与赵明诚志趣相投伉俪相得,在人们眼里是美满的天仙配,但在漫长的人生岁月中是不是也有不和谐的音律呢?诗为心声,词也是心音的流露。来看一首李清照的词《凤凰台上忆吹箫》:“香冷金猊,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任宝奁尘满,日上帘钩。生怕闲愁暗恨,多少事、欲说还休。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休休!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惟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云鬓斜簪,要与春花比美的李清照怎么连头也懒得梳了?新近憔悴,与酒与病无关,更不是哀叹岁月匆匆。这一段欲说还休的暗恨新愁到底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