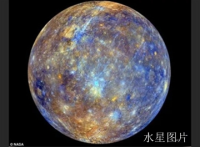婚姻美满的纯情少妇、丈夫出轨的中年怨妇、再婚又离异的悔恨孤独女、永念第一任丈夫旧情的寡妇......似乎一谈到婉约派词人代表李清照,总会有人为她贴上这样的标签。
在作家路也看来,如果让李清照听到这些形容,她定会慨然大喊一句:“余不耐!”就像女词人笔下争妍斗艳的花,真实的李清照一生都在与命运PK。她赌书泼茶、写文怒骂丈夫、公公甚至朝廷,在男性主导的环境下保持独立,保持质疑。
仅用“才女”一词来形容、指代和看待李清照,是把她大大地缩小和贬低了。这名旷世难遇的女性,不仅有才华,更有性情,她追求的不仅是爱情,还有更广阔的自我。活过、爱过、疯过,李清照用诗词告诉我们,人的生命,当同花儿一样饱满到充溢。
本文摘选自《蔚然笔记》,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经出品方授权推送。
李清照的花
(节选)
文 | 路也
一、关心花儿的胖瘦,让我认出了李清照
我读过一本翻译成英文的宋词选本,译成英文之后,几乎所有无比熟悉的宋词都戴上了万圣节面具,辨认不出是究竟是谁写的,以及究竟是哪一篇了,宋词在英语里忽然变成了一锅粥。
无论哪个作者,一眼望去,全都是愁云啊、断肠啊、登楼拍栏杆啊,向远处望望情人来了没有啊。这说明词体文学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脱离个人经验而依照传统题材创作的习气。
比如,热衷于描写孤独女性形象,同时重音乐并且具表演性,那么内容单一且格调雷同也就在所难免了,易辩认的往往是那些既有文体自觉,又能挑战题材格式的作品,比如,“塞下秋来风景异”那与众不同的外部场景让我认出了范仲淹。
写到花时,关心花儿究竟是瘦了还是胖了,让我认出了李清照,那是鲜明的个人经验:“绿肥红瘦”“人比黄花瘦”“杏花肥”,还是她的与花儿有关的一首词,写到“满地黄花堆积”的那首《声声慢》,其中的个人语调如此独特、鲜明、强烈,以至于谁也无法替代,即使将象形文字改头换面成拼音文字,也会让人一望便知:
“Search. Search. Seek. Seek. / Cold. Cold. Clear. Clear / Sorrow. Sorrow. Pain. Pain.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这些句子无论译成何种语言,在宋词里面依然有着很高的辩识度——毕竟是李清照啊。
在现能寻到的包括存疑在内的差不多70篇李清照词、诗、文及残句之中,未曾提到植物的花朵部位,而只是作为草树来涉及的植物,其实很少,大致有柳、桑、麻、梧桐、芭蕉、荔枝、银杏、柑橘、棠棣、扶桑、松、椿、荠菜、历荚草、田字草、白芷、兰草,对于它们,不仅所提次数少,笔墨也几乎全不用力,只是点到为止。
而相比之下,李清照对于花儿不仅写得多,所用笔墨也是浓重的,恨不得首首词都写花,至少要涉及到花。
当然,她写过的花儿品种并不广泛,只是大致集中了常见的几种类别,具体情形是:
涉及梅花的有20首,涉及荷花的有6首,涉及菊花的有5首,涉及桂花的有4首,涉及梨花的有3首,涉及海棠、荼蘼的各有2首,涉及牡丹、蔷薇、桃花、杏花的各有1首。
李清照写花儿的时候,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她喜欢让花儿们互贬,通过PK来决胜负。
她在一首专咏桂花的词里写道:
“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梅定妒,菊应羞,画栏开处冠中秋。”(《鹧鸪天·桂花》)
看看用的这些词吧,又是“第一流”,又是“冠中秋”,真够高调的,同时为了让桂花在名次问题上心中更踏实更笃定,还需要更进一步地把同行们贬低一番心始安,贬低谁呢?当然是就贬那风头劲的梅和菊了。
可是,在另外一首专咏梅花的词里,当写到月光下雪地上的梅花时,词人竟又说“造化可能偏有意”,还说“此花不与群花比”,硬是把梅花提亮并突出,放在了傲睨群花的位置。那么,一会儿桂花顶尖,一会儿梅花至上,这不是自相矛盾嘛,到底谁才是花中那名副其实的NO.1呢?
既然第一流的桂花,使得“梅定妒”,那应该是桂花赢了梅花了,可是,人家梅花接下来表态了,态度鲜明:“此花不与群花比”,看吧,人家梅花骄傲着呢,不搭理你桂花,不搭理任何花儿,梅花独自开放在茫茫雪地,有什么花儿曾经跟梅花同行过吗?
没有,从来都没有,人家梅花干脆不进入比赛!“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所以,最后,还是梅花赢了吧。
不仅花儿与花儿之间,甚至人与花儿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比试。
从卖花担上买来了一枝梅花,“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减字木兰花·卖花担上》)。
这是女人与花朵之间的PK,鉴于自古以来就有女人与花儿之间的相互比拟,女人也是花儿,所以这样的例子仍旧可以看作是花朵与花朵之间的比竞。
另外,还有花、物、人混合PK型的。
那个时候的菊花大多为黄色,故菊花也叫黄花,但是也有白色的菊花。李清照有一首专门咏白菊的诗,她先是拿白菊风姿PK杨贵妃,拿白菊容貌PK孙寿,紧接着又拿白菊气味PK韩令所获之奇香,拿白菊之色PK徐娘脂粉之色,遂得出结论,白菊清高得很,与那些人和事物全无可比性。
这样从人世间角度进行了全方位比较之后,作者仍嫌不够,又追加补充上了用花朵同类来相较,用白菊PK荼蘼,“微风起,清芬酝藉,不减酴醿”(《多丽·咏白菊》),酴醿即荼蘼,就是说,风吹来时,白菊清香徐徐,一点儿也不亚于荼蘼花的香气。好一个“不减”,虽未说出白菊和荼蘼到底谁赢了谁输了,至少是二者打了个平手。
荼蘼是一种可以直立也可以攀缘的灌木,从大范围上可以划进蔷薇科,开出重瓣层层的白色花,有黄色的蕊——荼蘼几乎是整个春天里最晚开的花,意味着春已尽而花季逝去——荼蘼花开,爱到荼靡。
这种花儿与花儿之间互相比试甚至互相贬低的写法,以及偶尔造成逻辑上的前后小矛盾,更反映出女词人并不执着于一时一事,也不擅长瞻前顾后的天真可爱的性格。
这种在笔下让花儿们之间进行PK的情形,有时候还会反映在李清照的其他作品以及现实行为之中。当然她是无意识而行,并无真正具体争竞之目的和目标,更无关乎功利,性格太鲜明的人难免会偶露峥嵘吧。
李清照如此,很可能源自她本人的批判型思维和直率性情,也与对个人才华的自信有关,最后一个可能的缘由是,无他,只关乎好玩和有趣。
“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既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金石录后序》)
这是赌书泼茶的青州往事,是一个阅读的记忆力比赛,谁先说出典故在书中所处具体位置,谁就先饮茶,李清照自称博闻强记,已暗示自己常为赢家。
当然还有野史中那个可能是虚构的著名故事,传说赵明诚读了清照词《醉花阴》之后起了比试之心,遂三天三夜苦吟出了一大堆作品,与清照那一首掺和在一起,匿名找人评判,结果人家只挑出了清照的“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李清照完胜。
还有“明诚在建康日,易安每值天大雪,即顶笠披蓑,循城远览以寻诗。得句必邀其夫赓和,明诚每苦之也”。被邀请和诗的人知道自己必输,怎能不苦恼,连重在参与的心境都没有了。
在写梅花的那首《孤雁儿》开头,有一个小序:
“世人作梅词,下笔便俗。予试作一篇,乃知前言不妄耳。”
就是这么狂,但狂得有资本,有道理,世人又能拿我怎么着?这如同她在《词论》中的做派和口气,把当朝最大、最著名作家一个也不放过地贬了一通,给他们上了一课,课程名字叫:创意写作+文学概论,究其实,此文从头到尾都隐含着一句未说出来的话,这话都快到嘴边了:
你们都到一边凉快去,下面就看我李清照的!
有一件事情,算是体现李清照智力优越和好胜心爆棚的一个集大成者,她终生沉溺于当时一种类似赌博的游戏:打马。她既有实践又有理论,为此写过一卷并不打算拿去评职称的专著《打马图经》。

李清照所著打马图经
这种游戏需要拼智力,很烧脑,但李清照喜欢挑战。
“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昼夜每忘寝食。但平生随多寡未尝不进者何?精而已。”
看看吧,已经自己承认天性好赌,每赌必赢。
丈夫赵明诚作为父母官面对叛军时只顾个人性命,续绳弃城逃跑,可够丢人的,李清照那首“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之诗,当是对此事略有讥讽,但或许自勉成分应当更多一些吧,活着要做人中豪杰,死了也要成为鬼中英雄,着眼于“杰”字和“雄”字,很难说不是在与整个人世乃至整个人类历史在PK。
李清照确实存在着一种PK思维。
二、李清照已经活成了梅花那般模样
如果说人与花之间存在着比拟的话,哪一种花更像李清照?或者说李清照的气质和性情更接近哪一种花?
我觉得应该是梅花,当然是梅花,那孤寂傲然、倔强不屈的梅花,那是风风火火的花,不要命的花。只有梅花敢于跟全天下的花儿进行PK。
李清照最著名的词其实并不是涉及梅花的,反而是涉及菊花、海棠或荷花的——这与作者本人无关,作者只管写作,决定不了作品的传播和接受。
但是,不能忽略的是,梅花是在她笔下出现得最频繁的花,比其他花都频繁得多,其他花儿出现次数相加在一起,大约能抵得上她写梅花的次数。这种现象完全是下意识所为,运用格式塔心理学的异质同构理论可以来解释这种现象,梅花这个外部事物与李清照的性情、人格、人生经历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
可以肯定地说,李清照具有非常典型的梅花人格和梅花性格。梅花在隆冬或早春孤单地开放,梅花只独唱不合唱,梅花不当乌合之众,梅花敢于顶撞风和雪,这些特征在李清照身上也很明显。
父亲李格非在党派之争时受连累,李清照以儿媳身份请求当时正做宰相的公公救救自家父亲,不料对方不理不睬,李清照寄去一首诗怒骂:
“炙手可热心可寒”。
李清照也骂丈夫,指着鼻子破口大骂。
在《感怀》一诗中,她说在莱州任上的赵明诚“青州从事孔方兄,终日纷纷喜生事”,骂丈夫中年油腻,奔波于酒宴之间,醉心于钱财之中,成天价无事生非。一言以蔽之,李清照嫌弃赵明诚俗!
她没有因夫妇二人均为公众人物以及自己的官太太身份,为了顾及影响和面子,就掩藏起个人好恶,而是率性而为。精神格调远远高于夫君,这不能不说也是她的悲愁之一。这样写诗当然体现了夫妻二人关系平等,同时也展示出女方更强势。
这差不多相当于现在有女诗人写了一首骂自己官员丈夫的诗,发表在了《诗刊》上,又做成了公众号推文,发至朋友圈,被各方转载,点击量想必会在十万加。
《金石录后序》里更可以看出李清照性格既爽脆斩截又不乏幽默的一面。她对赵明诚的态度很真实,有尊敬、有爱,也有讽刺和怨气。从对其性情了解这一方面,可算是对词作进行了一番补充。当写到起初二人世界中那奇文共欣赏的情形,那单纯的学术热情是颇令人留恋的,笔下充满了怀念和爱意,但是随着事态发展,对于金石的认识和鉴赏的闲趣,渐渐走向了占有,竟至走向极端和贪婪,不得不考虑其市场商业价值……
人在不知不觉之中就被这些外在的器物所异化,她开始质疑收藏那么多笨重古物是不是荒唐和愚昧,丈夫这种收集癖好未必就比其他癖好更高明,而且在石鼎器物上拓文并为它们写录注的结果,对后世很可能没什么效果和意义。她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帮助了丈夫,最后为此书刊行还写了这篇后序,但她依然保持独立看法,保持质疑。
说到底,她并不认为丈夫有多么了不起,她并不以丈夫为天,并不像这个文化中的绝大多数女人那样看重丈夫的事业。
对于后来藏品越来越多,需分类、收藏、封锁,不可以随意翻动,在动用那些书籍碑文时,得按要求循规蹈矩地爱护和擦拭,人竟沦为了东西的奴仆,失去了从前的阅读研讨之乐,李清照感受到了赵明诚被异化,而她不想被物所役,直接反抗,于是这个单纯girl直接就表示“余不耐”!带着十五车金石走在逃难途中则更加可怕,丈夫嘱咐在逃难中应按照书画善本古器藏品的重要性兼贵重程度等排序来决定去留,并郑重表达信任与托付:“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此处的宗器,有说是金石藏品中最贵重的,也有说赵氏家族宗族礼器的,反正是最不可放弃的。
敏感的李清照似乎意识到了自己被要求与这些宗器共存亡时,她这个人实际上也已经被物化并标识了价位,而且丈夫在遗嘱中只嘱咐宗器问题而略去了家产问题,这个男人其实是有些不靠谱的,他脑子一根筋,把自以为的伟大事业凌驾于他人的人生以至于性命之上,他自己快不行了,还是忘不了给老婆给添麻烦,让一个弱女子,在兵荒马乱之中,带着这些简直称得上后患的东西,奔波流离,万一遇上图财害命的,怎么办?赵明诚实在是不知被什么糊了眼,不分主次,思维出毛病了。
李清照写到这里,语调几近控诉了,直接表达“余意甚恶”。
在结尾处她似乎有引发联想的意图,试表明赵明诚这种行为跟梁元帝、隋炀帝以至于宋徽宗全神贯注于收藏器物而致亡国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两样,是一种价值颠倒,她差不多是在告诫大家不要学赵明诚哦。
唉,读到这里,竟感觉李清照使劲忍了忍,才没有模仿并套用谢道韫抱怨那才学低于自己的丈夫王凝之的口气去说话,是的,只差来上这么一句了:“不意天壤之中,乃有赵郎!”这篇本来是在亡夫著作出版时对书和人进行褒扬的文章,中间部分的细节回忆写得颇像小说,最后竟以劝诫而终,好不热闹。
当然,李清照还上告过第二任丈夫张汝舟,直接告到皇帝面前,坚决要求离婚,还我个人自由。
李清照有一些涉及时政的诗作,连当时的朝廷甚至包括皇帝也敢骂,先是挖苦,后几近训斥:
“土地非所惜,玉帛如尘泥。谁可当将令,币厚辞益卑。”(《上枢密韩肖胄诗二首·其一》)
李清照所经历的靖康之变,绝不亚于杜甫经历的安史之乱,国难当头,家祸不断……李清照为何悲愁,还用问么,何止是李清照在悲愁,半个中国都在南渡之中悲愁着!
李清照除了悲与愁,还有万丈豪情呢:
“木兰横戈好女子,老矣谁能志千里,但愿相将过淮水。”(《打马赋》 )
“嫠家父祖生齐鲁,位下名高人比数。当时稷下纵谈时,犹记人挥汗成雨。子孙南渡今几年,漂流遂与流人伍。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上枢密韩肖胄诗二首·其一》)
这分明是在写血书!
所以,既不该仅仅以那些闺中诗作来界定李清照,也不该将那些或清丽或温婉或凄清的闺中作品全都按照同一个通行路数来解读,认为全都与赵明诚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似乎赵明诚是恒星,李清照是卫星,李清照永远围绕着赵明诚旋转。
这些词当然可以跟赵明诚有关,但除此之外,其实也可以仅仅是传统题材的类型化创作,也可以是抒发与赵明诚无关的闲愁以及中年南渡后命运飘零的感慨。
当然啦,除了赵明诚和张汝舟,李清照是否还跟其他男子有情感互动,我们不得而知。李清照在赵明诚死后,又至少活了二十七年,甚至三十年以上。她那人生的后三十年,创作力依然旺盛,难道首首词都围绕着赵明诚?
用“才女”一词来形容、指代和看待李清照,是把她大大地缩小和贬低了。她是一个旷百世而一遇的人物,不仅因才华,甚至同时也因性格和性情而胜出——这性格和性情其实也是才华的一部分。
这确实是一位北方女子,确切地说,是一位山东女子。
齐鲁大地有一个很奇怪的特点,在文化上,这片土地基本上不出旖旎的才子才女,也很难出现一时扎堆的群星闪耀的局面,它甚至可以让自己在相当长时期之内都保持缄默和笨拙,似乎面无表情,但是,它的“地力”是足够的,甚至还有富余,它不出人物则已,要出,就只出那最大的和最猛的:先是给中国文化奉献了孔孟,然后又以一当十地生长出了二安。
可以随便想象一下历史,没有这个人或者没有那个人,对这个文化格局的影响都不会太大,这个文化依然还是这个文化,可是,你能想象这个文化里没有孔子和孟子吗?你能想象整个文学史里或者宋词里没有李清照和辛弃疾吗?

倘若没有了这几个山东人,整个文化结构甚至文化基因就会发生改变。
一些研究者专门从字缝里瞅李清照作品,产生了贤内助之说,婚后不育导致丈夫忍受不了丁克家庭而出轨纳妾之说,再婚离异名誉扫地致悔恨之说,后半生悲愁来自丧夫之说,终生对原配丈夫怀念之说……全都是没有历史事实依据并且背离文学创作规律的扯淡。
原来宇宙虽大,李清照喜怒哀乐必系于赵明诚之身,方被允许。一个女人文学天赋太高,而她所处的那个人文环境又缺乏对待这类特异女子的心理准备,于是她的存在就给男权社会带来了文化上的恍惚感和失重感,当世者和后世者倘不弱化一下她的能量,按照自己心目中期待的样子去重新塑造一下她,就没法儿接纳她,于是潜台词永远都是:天赋再高,也是个女人,如果不依附于某个男人就活不了,至少是活不好。
而实际上,李清照已经活成了梅花那般模样,梅花是最初的,也是最终的,梅花是永远的,梅花贯穿了词人的一生。梅花与李清照之间划上了等号。
梅花特立独行,大家都开花时,我不开,大家都不开花的时候,我偏要开,自己开,迎着风雪开放。李清照正是在男权的时代症候和历史话语之中挺立着和独立着,仅凭散佚之后留存下来的这些少数作品,这个女词人的幽魂仍然不得不面临着并抵抗着一波又一波庸俗社会学的阐释。
百花对梅花产生讶异和质问:你为什么偏偏要在冬天开花?
梅花反问:我为什么不能在冬天开花?
在李清照大量涉及梅花的词里,有两首特别值得注意。
对于《玉楼春·红梅》的末句“要来小酌便来休,未必明朝风不起”,有一种理解是女词人在对丈夫赵明诚讲了这番话,也就是说整体上又将此首词理解成了盼夫归,盼夫快快归来一起赏花,要归来呀,归来饮酒赏花,否则也许明天就起风了,就会把梅花吹落了……是的,有的人不把李清照理解成望夫崖或者神女峰,就不肯罢休。
而对于此句,我还读到另外一番理解,整个词的下阙包括这个末句则是由梅花对女词人说出来的,是梅花正对着女词人发出呼唤:你呀,你想来梅下饮酒么,就快快来嘛,你要是不快快来,敢明儿我可能就凋落了呢。
联系上下文,这意思完全讲得通——这番解释,才体现出女词人的风趣和格调来,也甚合我意,当也合此首词中梅花的心意,对于李清照,梅花是真朋友,是好姐妹,是闺蜜。
《清平乐·年年雪里》当是李清照涉及梅花的词中将梅花写得最好的一首。这首词当作于晚年。
在这首词中,词人把咏梅的调子弹拨到了最强音,使得梅花成为了词人一生的线索。从过往的“年年雪里,常插梅花醉”到如今的“看取晚来风势,故应难看梅花”,这之间的跨度是整整一生。
家世非凡,年少成名,柳絮才高,激扬文字,夫妇相和,岁月静好,靖康之变,天堂地狱,负重南渡,金石散去,夫死独立,再婚再离,江山半壁,北归无期,颠沛流离,韶华逝去,沧桑历尽,恍如隔世,气若游丝,万物向死……
当感叹“今年海角天涯,萧萧两鬓生华”的时候,她是不是还忆起了少女时代“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
人生最初的梅花和人生最后的梅花,就这样首尾呼应着。

赏梅的最早记载大约开始于汉朝,但是,梅正经八百地作为一种观赏性植物而存在,还是进入宋朝以后的事情。
植梅成风,赏梅成风,是全社会热衷花艺以及吟诗作画大潮流里的一个侧面,据说与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之后的“偃武修文”有关,也可算得上是官方倡导了。李清照词中提及“酒美梅酸”,这里面的梅子显然是当作代替食醋的调味品来使用着的,但是除此之外的其他词作中的梅树和梅花,无论野梅还是种植梅,从词人角度,均是为了审美而存在的。
梅,毫无疑问一般指的都是蔷薇科李亚科杏属的梅,小乔木或者稀灌木,有红梅、粉梅、白梅或者其他颜色的梅。那么,除此之外,还有蜡梅,蜡梅科蜡梅属的灌木,专开黄色蜡质花儿的那种,是不是也可以勉强算作梅花或者充当梅花呢?
二者不同科不同属不同种,却由于开放时间相同,常被混为一谈,文人毕竟不是科学家,不必责怪。我认为李清照在词中所写的梅基本上都是第一种梅,可是,会不会偶尔也会包含了第二种梅——蜡梅?
李清照写梅花时,大多时候是在普遍意义上写到了梅花,想必是红梅或者白梅吧,兴许还有蜡梅。而有时候她又会特别点明是“江梅”:“江梅些子破,未开匀”、“江梅已过柳生绵”、“手种江梅渐好,又何必,临水登楼”,据说江梅是一种没有经过人工培植的野梅,大多开得比较早,自己生在山间水滨,尤其有荒寒清绝之美。
那么,“手种江梅渐好”是什么意思?李清照自己从野外移了一棵野梅栽种在自家后院里了么?
外表模样阴阴柔柔的,而内心却可以是阳刚的和顽强的。这样的梅花,或者说这样的女子,这样的诗人,要风情有风情,要豪气有豪气,还发脾气,好胜,但是,有趣。
李清照写的梅花,是“我的梅花”,是与人生同步的梅花,有着词人的喜怒哀乐的梅花。
三、对花的爱,来自对生命的热情
说完了李清照的梅花,再来看看她写的其他的花。
当然,在涉及花的词作中,最有名的,是她那涉及海棠、菊花和荷花的。
她写海棠,用一首短短的小令,就把海棠轻而易举地写成了经典,将海棠直接送进了文学史,再也出不来了。
《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中通过女词人跟侍女之间的对话发生,增强了这首词的戏剧性,这场关于海棠花的对话场景的发生,时节应该是在春末夏初吧。词人不满于侍女那个刮了一夜风一夜雨之后“海棠依旧”的答案,认为对方明显是对于事物缺乏观察力和感受力或者态度敷衍,于是宿醉刚醒的慵懒一下子变成了劈头盖脸的驳责。
“知否,知否,”整个这首小词中的对话与其说是疑问性质和反问性质的,倒不如说是设问性质的,女词人心中早已有了一个预设的答案,只不过故意把侍女拉进对话,好让自己把正确答案大声地出来:“绿肥红瘦”——这高度概括的四个字,写尽暮春,写尽风雨,写尽海棠,同时也算写尽了人。词中貌似并没有以花比人的意思,其实在情境上还是有所比拟的,若细细深究的话,字里行间深深隐藏着一个“海棠春睡”典故,用于统领全篇却丝毫不露痕迹,从宿醉浓睡之中刚刚睡醒过来的女词人当时的身心状态,颇似醉酒后初睡醒的杨贵妃,据说当时唐明皇见到贵妃那副慵懒之态,评论道:“岂妃子醉,直海棠睡未足耳!”海棠竟是会睡眠的,并且醒来时有着心慵意懒的风致。
男人夸女人,夸得这么高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苏东坡写“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海棠》),因担心海棠花睡去,故夜间点起蜡烛来赏花,就涉及了这个典故。
在李清照这首词里,女词人形象本也是慵懒的,却由一个自我随意设计的小型对话引出来了诘问和纠正,从而打破了这种慵懒,使得词人一下子清醒过来了不少,顿时显露出了常态里的年轻任性和伶牙俐齿,词中的抒情主人公可谓一派清新,就像那海棠的叶与花一样,闪烁着琉璃的光泽。
李清照写菊花,就像她写海棠一般好。
她写菊,小部分原因,是向陶渊明致意,不排除有比德之念。花已被陶渊明占领并圈了地盘,李清照写菊花其实并不比陶渊明写得差,可是也只能让贤了。她见到菊花难免会想起陶渊明:“细看取,屈平陶令,风韵正相宜”、“人情好,何须更忆,泽畔东篱”、“不如随分尊前醉,莫负东篱菊蕊黄”,言必称陶或者在暗示陶,李清照写的菊花仿佛是陶渊明家的菊花。
但是,李清照写菊的绝大部分原因,其实只是为了借晚秋初冬时节的菊花来表达个人心境,尤其是生命中的憔悴之感以及悲伤之意。这使得这些词中的菊花,几乎具有了人类的体温和生命的深度。
《醉花阴》里的菊花是这样的: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写到了菊花的香气,又写到了那形销骨立之人,把帘外菊和帘内人联系在一起的,则是一阵寒凉的西风……那人跟那菊花可有一比,她有菊之态、菊之意、菊之孤零、菊之独立秋风,这首诗写得忧郁甚至抑郁,却并不郁闷,想必那一阵西风在吹起门帘时也将人的心灵一角吹起了。
到了《声声慢》里写菊,这忧郁或抑郁的压强则加大了,成了悲苦。从开头那个“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句子可以猜测得出李清照的肺活量很大,很可能在3500至4000之间,否则这样用一口气来表达情绪的极端句式会把自己憋坏。这样用叠字叠词一上来就把全诗的基调确定下了,把大致氛围给铺垫好了……
于是,菊花登场,“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
可以看出,从《醉花阴》到《声声慢》,程度全方位加重,凉意变成了凄风苦雨,那原本有着暗香的清瘦的菊花而今则几乎全都凋残委地了,即使尚留枝头的,也枯萎得没几朵可摘的了,孤零忧郁已经演变成了悲怆,那个比黄花还瘦的人如今已经走到了人生绝境!
在这类充满了个人生命体悟的词作中,菊花对于李清照意味着天起凉风日影飞去,意味着形单影只和丧失。
这类菊花词作中的那个或侧面或正面的形影,体现出来的韵致,倘若套用一下戴望舒诗作的意境,或许也是可以的呢:这个有菊花一样的颜色、菊花一样的芬芳、像菊花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她在西风里哀怨,哀怨又彷徨,最终,在西风里消了她的颜色,散了她的芬芳。

荷花对于李清照,是与快乐有关的花,荷花给女词人带来的几乎全是快乐的经历,并留在记忆里。
女词人写荷花,写了夏天的或者秋天的荷花,往往又都与泛舟的情形相连。
像《如梦令》里的“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
像《双调忆王孙》所写“湖上风来波浩渺。秋已暮、红稀香少”。
还有像《一剪梅》里的“红藕香残玉蕈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那叙事者应该也都是泛在舟上的,甚至是独自行动,而水中总是开满了荷花。
这些词基本上都是快乐和清爽的,每个字仿佛在水中洗过一般。《如梦令》里的那个在溪亭日暮中划船的女子,大概率是喝酒贪玩,天黑下来了,她还不肯回家,把船不小心划到了荷花丛中去了。
《双调忆王孙》写的虽是晚秋,“莲子已成荷叶老”,却丝毫没有传统中的悲秋之意,字里行间透出一种风轻云淡的快活,至少也算是自得其乐,同样是玩得不想回家了,明明贪玩,这次却赖到鸥鹭身上,觉得鸥鹭挽留自己,不愿让自己走,“似也恨、人归早”。
《一剪梅》里虽有“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相思,但也只是一种幽幽的期盼和淡淡的迷惘,不过是散淡悠然情绪之中的某种调味吧,依然是美好的,潜意识里有着某种自我满足和小惬意。
《浣溪沙·绣幕芙蓉一笑开》里也涉及荷花,虽然只是间接涉及荷花,更与泛舟无关,但写的也是快乐之事,是约会调情。有人疑其为伪作,我看倒未必。
同时代有那么多男词人都在写狎妓之作,谁规定了作为女人的李清照——在预设和臆想之中被要求单方面成为中规中矩爱情的楷模——不可以调情?何况自自然然、健健康康的男女关系包括夫妻之间都应该是很放松的,完全可以非常活泼以至于可以调情的,举案齐眉则实属反常。
同时代王灼对李清照既夸又贬:
“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搢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籍也。”
从反面印证了她确实写过所谓调情之诗。在这首词中,其实没有直接写荷花,只是借荷花来写了一位女子,这位女子脸庞因为爱情而成了一朵莲花正在盛开!多么明丽!开篇即读到此句,禁不住想起了徐志摩的诗: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但是到了后来,估计是南渡之后的中年以后岁月,她依然写着荷花,只是在那荷花上寄托了惆怅,为什么惆怅,只因那荷花意象引发了她对旧日快乐时光的回想:
“翠贴莲蓬小,金销藕叶稀,旧时天气旧时衣,只有情怀不似、旧家时!”
这里写的荷花,也是间接涉及,不是生长在水里的,而是在一件衣裳上面绣着的。这首词《南歌子》,上阕提到“罗衣”,下阙就点明这是一件绣了花的织物,是用贴翠和销金这两种工艺绣制,即以翠羽贴成莲蓬样,以金线嵌绣莲叶纹,而现在衣服旧了,翠羽和丝线均有所脱落和松散,致使莲蓬看上去变小了,荷叶也变得少了,这以羽贴和丝线绣制出来的莲蓬和荷叶均来自手工,制作它的人和穿起它的人都在上面有所寄托,人的欲望和记忆就隐匿在这些几何图案里……
就是这样,一件旧了的织物绣品成为了流逝了的旧时光的具象载体——那旧时光里,那记忆里,一定有年少时“误入藕花深处”的欢乐吧。时光留不住,能留下来的这件代表往昔的旧衣服,它是往昔曾经存在过而又变得模糊,再也不能回返的一个证据。抚摸这件图案已经黯淡脱落的旧衣裳时,感到人生多么虚幻。
李清照的荷花,几乎全是快乐之花,即使偶尔表现出了惆怅,其实也跟突然忆起了旧时的快乐有关。荷花似乎总是和泛舟有关,泛舟又总与快乐有关……这快乐终随时光而逝,只剩下了回忆,成了一件绣着荷花的旧衣裳。
荷花是快乐的,女词人曾经也是快乐的,活过、爱过、疯过……最后,依然清如水。
而无论如何,李清照喜欢花儿,则是千真万确的。为什么李清照那么偏爱写花呢?花儿不像岩石、泥土、天空、太阳、月亮那样具有永恒和冷漠的特质,相反,花儿总体上是热情的、敏感的、脆弱的、短暂的,跟人的生命和青春具有相同特质,这一点,非常重要,花朵开放的欣喜里面已经包含了凋零的忧伤,盛开并且凋零,这是花朵的使命。
花朵在盛开并且凋零的过程之中,朝向永恒。花朵的价值观就是美的价值观。
对花儿的喜欢,正是从对于生命的热情而来。这是一个饱满到充溢的生命,而不是一个总是皱着脸的苦哈哈的弱弱的人儿。
有一种由来已久的既奇怪又病态的“凄苦诗学”,凄苦形象特别容易招人待见,满足人们的某种隐蔽的心理需求,大家或明或暗地在配合着。某些研究者企图把李清照塑造成“婚姻美满的纯情少妇+丈夫出轨的中年怨妇+再婚又离异的悔恨孤独女+永念第一任丈夫旧情的寡妇”,读类似所谓专著时,我直想模仿李清照的语气喊一声:“余不耐!”
弗洛伊德说:“美的短暂性提高了美的价值”。那些花朵和女词人本人一样,虽已在时间里逝去,却通过诗词而获得了不朽。
某个春夜细雨中的一树梨花、某个夏日湖上的一丛荷花,以及某个冬日江边飞雪中城墙下的一枝梅花……
它们可知晓自己会穿越过八百年,来到今天,来到我的灯下?
本文节选自《蔚然笔记》
作者: 路也
出版社: 花山文艺出版社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年: 2022-9
原标题:《关心花儿的胖瘦,让我认出了李清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