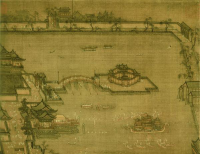苏门后四学士
宋代李格非、廖正一、李禧、董荣的并称。继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之后,上述四人被称为“苏门后四学士”。他们的文学理论和诗文创作都颇具特色,与前“四学士”一样,他们也是苏轼文学的传人,元祐文坛的中坚。 (出处《涧泉日记》)

苏轼 (1037年-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画像

李格非(约1045年—约1105年),字文叔,齐州章丘(今山东济南市章丘区 )人,北宋文学家,李清照之父。
廖正一 (约1060年—约1106年)字明略, 号竹林居士 安州(今湖北安陆)人。主要作品 《白云集》、《竹林集》。神宗元丰二年(1079)进士(明嘉靖《延平府志》卷一七)。哲宗元佑二年(1087),为秘书省正字。六年,除秘阁校理(《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之一二)。绍圣二年(1095),知常州(《咸淳毗陵志》卷八)。入党籍,贬监玉山税,卒。 少时为文,藻采焕发,黄庭坚称之为“国士”。元丰二年(1079)成进士,授华阴司理,累官端明殿学士,后出知常州郡。与苏轼交游最善。撰有《白云集》、《竹林集》,已佚。
哲宗元祐二年(一零八七),为秘书省正字。六年,除秘阁校理(《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之一二)。绍圣二年(一零九五),知常州(《咸淳毗陵志》卷八)。入党籍,贬监玉山税,卒。工篆书,元祐八年(一零九三)僧道潜所书新城普向院我宝佛塔记,为其所篆额。《东都事略》卷一一六有传。今录诗七首。
少时在凌岩山读书,爱品茶,趣味高雅。中进士入京官拜端明殿大学士。苏东坡当时为品茗大家,家有御赐的密云笼供茶,只与“苏门四学士”共品,他人无此殊荣。一日客至,东坡命取供茶,童子上茶,见是廖正一,深感意外。其实东坡素爱正一的才学与茶品,曾以《行香子》一词录赠他,有“共夸君赐,初拆臣封,看分香饼、黄金缕,密云笼,斗赢女功敌千钟,觉凉生,两腋清风”之句,词录在《东坡集》中,可见廖正一不愧茶乡蒲圻人,能与东坡煮茶、品茶、斗茶,达到“两腋清风”的品茶入仙境界。

廖氏在四库全书,氏族大全的记载/今湖北赤壁市(原蒲圻)中伙铺镇有廖正一墓。
廖正一《瑶池宴令》:
飞花成阵,春心困,寸寸、别肠多少愁闷,无人问。
偷啼自搵。残妆粉,抱瑶琴,寻出新韵。
玉纤趁、南风未解幽愠。低云鬓,眉峰敛晕,娇和恨。
李格非《书〈洛阳名园记〉后》:
论曰:洛阳处天下之中,挟肴渑之阻,当秦陇之襟喉,而赵魏之走集,盖四方必争之地也。天下常无事则已,有事,则洛阳必先受兵。予故尝曰:“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
方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余邸;及其乱离,继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树,兵车蹂践,废而为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为灰烬,与唐共灭而俱亡者,无余处矣。予故尝曰:“园圃之兴废,洛阳盛衰之候也。”
且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圃之废兴而得,则《名园记》之作,予岂徒然哉?
呜呼!公卿士大夫方进于朝,放乎一己之私意以自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乐,得乎?唐之末路是矣!
人物详情
宋韩淲《涧泉日记》卷上载:“廖正一明略、李格非文叔、李禧膺仲、董荣武子,时号‘后四学士’。明略有《竹林集》,文叔有《济北集》,膺仲、武子文集未之见也。”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四人,文学史上称“苏门四学士”,这已为我们所熟知;但据这条记载,当时还有“后四学士”,对此学界很少提及,更无人对他们进行专门研究。
按:韩淲(1159~1224),字仲止,号涧泉,祖籍开封,元吉子,南渡后居上饶(今属江西)。所著《涧泉日记》,现存《永乐大典》本,凡三卷,另有《涧泉集》二十卷传世。《四库提要·涧泉日记提要》称韩淲“人品学问,即具有根柢。……其亲串亦当代故家,如东莱吕氏之类,故多识旧闻,不同剿说”。则其为人为学都可信赖,所言廖正一等“时号‘后四学士’”,必当有所据依。只是四人文集散佚,其中李禧、董荣两家的史料遗存极少,作为一个文学群体,长期为历史的尘埃所掩,便几乎从研究者的视野中消失。唯其如此,更有发掘和考察的必要,否则,许多研究就难免存在缺失,比如苏轼文学集团的核心,一般就只知是“四学士”或“六君子”。本文拟钩沉发覆,考述廖正一、李格非等四人的生平事迹、著作及与苏轼等人的关系,并略论他们的文学思想及创作成就,以求对“后四学士”有较多的了解。
“后四学士”事迹著作考略
据上引《涧泉日记》,“后四学士”的领衔人物是廖正一。廖正一,字明略,安州(今湖北安陆)人。元丰二年(1079)进士。元祐二年(1087)除秘书省正字,六年,除秘阁校理①,通判杭州(见孔武仲《举自代》,详下引),绍圣二年(1095)知常州②,入元祐党籍,贬监玉山税,卒。《东都事略》卷一一六有传。
今存邹浩《雪廖正一奏状》,为我们了解廖氏知常州时的遭遇,提供了重要补充:“伏见前秘阁校理廖正一文高学博,望著一时,性介少容,多取怨嫉。昨知臣乡里常州日,恩威并行,善良得所,父老劝诵,谓近年以来少见比拟。只缘不能曲奉本路监司,为其深怒,遂以锻炼惨酷,造成正一赃滥等事,士民痛愤,为之流涕。近虽蒙朝廷引用累赦许令叙复,然暧昧之罪,尚未昭除。……伏望圣慈特降指挥,选官置司,别行根勘。”③ 苏轼晚年由儋州北归,在《答廖明略》(其二)中,对此案也很关心,曾满怀同情和信心地说:“毗陵异政,谣颂蔼然,至今不忘。为民除秽,以至虿尾,吴越户知之,此非特儿子能言也。圣主明如日月,行遂展庆,众论如此。”④ 无论“根勘”结果如何,廖正一这颗文苑政坛“文高学博”的明星,在党祸时期残酷的政治清洗和官场内耗中,已不可能有多大作为了。
廖正一的卒年,文献阙载。考吴则礼《北湖集》卷四有《予谪居荆南,赋诗百馀篇,书为两轴。丙戌(崇宁五年,1106)夏,泛舟归润,道由汉阳,廖明略邀予饮于郎官湖,因携示之。明略坚欲抄录,会予舟行甚速,期以他日见归,不幸明略死矣,此本不复可得。……因感而有作》诗,诗曰:“三年放逐臣,今复得归去。梦已到南徐,船回正鸣橹。”“南徐”即润州(今江苏镇江)。细味诗意,作此诗时尚未抵达润州,而知廖已死,则廖正一卒年,当即在崇宁五年的夏秋。常州案是否得以“根勘”,“根勘”后廖氏是否得以昭雪,其在汉阳是否有职任,皆不可详。
廖正一的著作,《东都事略》本传称“有文集十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一九(衢本)著录“廖明略《竹林集》三卷”,谓“绍圣间,明略贬信州玉山监税,郁郁不得志,丧明而没。自号竹林居士”。《文献通考》卷二三七同。所述过简,且上引吴则礼谓其临终前尚“坚欲抄录”诗稿,则“丧明而没”显然失实。晁氏所录,从集名判断,当即韩淲所见的本子。但《宋史》卷二○八《艺文志七》又著录“《廖正一集》八卷”。则廖氏文集,宋人著录有十卷、三卷、八卷三种,集名也不相同,盖有多种版本传世。《全宋词》小传谓廖氏“有《竹林集》三卷(或云有《白云集》)”。按《瀛奎律髓》卷二○收廖正一《和补之梅花》诗,方回称“有《白云集》”,唐圭璋先生盖据此。又佚名《排韵增广事类氏族大全》卷一八,亦谓廖正一“有诗文号《白云集》”。考宋何汶《竹庄诗话》卷一○收黄庭坚《次韵廖明略陪吴明府白云亭燕集》诗,释道潜也有《与廖明略学士赋余干县白云亭一首呈吴明府》⑤ 诗,《白云集》是否与此“白云亭”名有关,已不可考。各集皆散佚已久,《全宋诗》仅辑得佚诗七首,《全宋文》也辑文不多。
李格非,字文叔,济南(今属山东)人。熙宁九年(1076)进士,调冀州司户参军。试学官,为郓州教授。入补太学录,再转博士。绍圣立局编元祐章奏,以为检讨,不就,戾执政意,通判广信军。召为校书郎,迁著作佐郎、礼部员外郎,提点京东刑狱,予祠。崇宁元年(1102)七月入元祐党籍,罢。⑥ 卒,年六十一。《宋史》卷四四四有传。
李格非是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之父,其著作,晁氏《郡斋读书志》卷九、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八仅载《洛阳名园记》一卷,而未录其文集。据陈氏说,其“集不传,馆中亦无有,惟锡山尤氏(袤)有之。《(皇朝)文鉴》仅存此跋(按指《书洛阳名园记后》),盖亦未尝见其全集也”。尤袤所藏本,疑即韩淲所说的《济北集》。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卷三称有“诗文四十五卷”,当是《济北集》的卷数。明焦竑《国史经籍志》卷五著录《李格非集》四十五卷,盖即据《后村诗话》。文集也已久佚,《全宋诗》辑得佚诗九首、零句二,《全宋文》辑文也不多。又,《玉海》卷三九载李格非《(礼记)精义》十六卷,另著有《历下水记》,见《墨庄漫录》(详下引)。
至于李禧、董荣二人,文献所载极罕,生平已不可考。按孙绍远《声画集》卷八载李膺仲《题自画芦雁》诗:“晚来无声理扁舟,唤起骚人漫浪愁。过眼飞鸿三两字,淡烟寒日荻花秋。”《全宋诗》卷一一九九收此诗,小传曰:“李膺仲,约神宗、哲宗时人。”据《涧泉日记》,作者当以“李禧,字膺仲”为确。《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九载苕溪渔隐曰:“词句欲全篇皆好,极为难得。……董武子‘畴昔寻芳秘殿西,日压金铺,宫柳垂垂’。然秘殿岂是寻芳之处?非所当言也。”《全宋词》收此零句,案称“此数句似是《一剪梅》词残篇”,小传谓“董武子名耘,或名荣。疑作耘为是”。按晁补之《永感堂记》⑦,记“东平董耘武子”孝亲事,唐圭璋先生盖据此。然董荣、董耘是否一人,尚无直接的依据,其人似当据《涧泉日记》作“荣”为是。⑧ 二人文集,韩淲称“未之见”,其实就连他们是否曾有集行世,也不可考。盖二人当时初露头角,便被波诡云谲的政治风潮所淹没,永远地消失了。
综观上述四人,廖、李(格非)二人皆登进士第,尝任职秘阁,唯李格非历官最高;后又同罹元祐党祸,而廖正一竟蹭蹬以卒。董荣也有馆阁(元丰新制,馆阁并入秘书省)经历,从上引其残词“畴昔寻芳秘殿西”句可知;而李禧既入“后四学士”之列,亦当尝入秘书省,唯现存文献阙载。
“后四学士”与苏轼及前四学士关系考
廖正一等四人,必须及苏轼之门,且在与苏轼的关系上,同黄、秦等苏门“四学士”有可比性,才有资格称“后四学士”。然因李禧、董荣事迹已不可详,故此所考,只能以廖、李二人为主。
按《东都事略·廖正一传》:“元祐中,苏轼在翰苑试馆职之士,得正一对策,奇之,除秘书省正字。……轼门人黄、秦、张、晁,世谓之四学士,每过轼,轼必取密云龙瀹以饮之。正一诣轼谢,轼亦取密云龙以待正一。由是,正一之名亚于四人者。”苏轼试馆职,在元祐元年(1086)十一月。上引晁氏《邵斋读书志》在著录《竹林集》时,亦曰:“元祐中召试馆职,苏子瞻在翰林,见其所对策,大奇之。俄除正字。时黄、秦、晁、张皆子瞻门下士,号‘四学士’,子瞻待之厚,每来必命侍妾朝云取密云龙,家人以此知之。一日,又命取密云龙,家人谓是‘四学士’,窥之,乃明略来谢也。”则廖正一乃苏轼所取士,与苏轼关系之亲密,在当时的声望,仅亚于“四学士”。苏轼在《答钱济明三首》(其二)中,有“某得来书,乃知廖明略复官”⑨ 云云,对其进退,也一直萦怀。许多年后,苏轼南贬北归时,有《答廖明略》书二首⑩,写心述怀,极尽款曲,流露出深厚的师友情谊。轼弟苏辙在为廖正一除秘书省正字所草制中,有“尔推言往古,以及当世,挺然不回”,“尔往讲习道义,长育才干,敦业以待举”之语,(11) 褒之亦至。
廖正一与前“四学士”,更是游伴兼诗友。他与晁补之为同年进士。《能改斋漫录》卷一六《晁无咎嘲田氏词》曰:“元丰己未(二年),廖明略、晁无咎同登科。明略所游田氏者,姝丽也。一日,明略邀无咎同过田氏,田氏遽起,对鉴理发,且盼且语,草草妆掠,以与客对。无咎以明略故有意而莫传也,因为《下水船》一阕……”此事又见《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三。既涉及私生活,可见两人关系之亲密无间。廖正一登第时,黄庭坚有《次韵晁补之廖正一赠答诗》,咏廖氏道:“十年山林廖居士,今随诏书称举子。文章宏丽学西京,新有诗声似侯喜。”又有《再次韵呈廖明略》,称“学如云梦吞八九,文如壮士开黄间”。又《再答明略二首》之二道:“廖侯言如不出口,铨量今古大如斗。度越崔张与二班,古风萧萧笔追还。”如此之类的次韵唱和诗,还有多首。(12) 则不仅晁补之,连黄庭坚也对廖正一赞之不置。苏轼曾在《与李昭玘书》中,对这些唱和诗作了很高评价:“观足下新制,及鲁直、无咎、明略等诸人唱和,于拙者便可阁笔,不复措词。”(13) 二十多年后的元符三年(1100)四月二十五日,晁补之作《跋廖明略能赋堂记后》,有曰:“余同年生廖明略,学问博古,志操如雪霜,然以方北郭顺子,则清而未容,故骜世患。”(14) 这时,廖正一已作古,作者在经历了太多的宦海风波之后,读罢老友文章,回顾往事,可谓百感交集。
至于李格非,《宋史》本传称其为太学博士时,“以文章受知于苏轼”。考苏轼于元祐四年(1089)七月出知杭州到任,元祐六年二月以翰林学士承旨诏归,五月下旬抵京,八月出知颍州。据徐培均《李清照年谱》,元祐六年“格非官太学博士,俄转校对秘书省黄本书籍”;“格非之任此职(指校对秘书省黄本书籍),当在本年十月哲宗驾幸太学之后”。(15) 则李格非为太学博士时,苏轼正在京师,他以文章受知苏轼,应在该年六至八月间。
但是,考苏轼在黄州所作《与文叔先辈》、《与李先辈》书三首(16),《与文叔先辈》(其一)称赞“新诗绝佳,足认标裁”,而苏轼贬黄在元丰三年(1080),可知两人早有交往。(17) 两人既然早在元丰间就有书信往来,何以至元祐六年才“以文章受知”?细节尚不详,盖相交与入门有所区别。
从以上所考可以看出,廖、李二人都是受知苏轼、或由苏轼直接简拔的文士,这与黄庭坚等“苏门四学士”相同,具备了成为“后四学士”的主要条件。黄庭坚为治平四年(1067)进士,秦观元丰八年(1085)进士,张耒熙宁六年(1073)进士,而廖正一与晁补之同年,李格非则是熙宁九年(1076)进士,还在秦观之前。除黄庭坚登科较早外,其余三人与廖、李可谓科第相先后。但是,黄庭坚于元丰元年(1078)即开始与苏轼通信,从此缔交。熙宁十年,苏轼时知徐州,秦观前往访之,成为门下士,并作有著名的《黄楼赋》。晁补之十七岁就曾随父拜访时任杭州通判的苏轼。张耒在弱冠登进士第之前,曾游学于陈,学官苏辙爱之,因得从轼游。他们追随苏轼并成为门下士,都比廖、李早。因此,就入苏门时间论,廖、李等晚于黄、秦等四人;后因遇元祐党祸,致使廖、李等接受苏轼的沾溉,也相应地较黄、秦等为少。在苏门以四人为单元的“方阵”中,他们只能居“后”了。
“后四学士”的文学思想
叶梦得《廖明略竹林集序》记廖正一言曰:
吾深服左氏,而乐道范晔之秀正温绎。晔尝自叙其书,以为“但多公家之言,而少事外远致”,吾所恨亦云。丘明不可及也,异时有置吾于晔伯仲之间,吾尚无愧。往有评吾文似尹师鲁者,吾虽不学师鲁,然意善其言。
接着,叶氏说:“是时余见明略文固多,知其所自道不诬也。”(18) 由知廖正一崇尚《左传》,甚至认为“丘明不可及”。所作文章,自认为与范晔“但多公家之言,而少事外远致”有同恨。廖氏的文章风格,时人以为似尹洙(师鲁)。《宋史》本传称尹洙“尤深于《春秋》”。欧阳修《尹师鲁墓志》谓其“为文章简而有法”(19),并在《论尹师鲁墓志》中解释说:“此一句,在孔子六经,惟《春秋》可当之,其它经非孔子自作文章,故虽有法,而不简也。”(20) 虽现存廖正一文章极少,我们可以推想,他的整体风格也是简古,即《廖明略竹林集序》所说的“曲奥简洁”(详下引),故其乐意接受“似尹师鲁”的评论。但他同时又追求“秀正温绎”,“事外远致”,故叶《序》又谓“音节遒峻,精新焕发,使人读之,不觉矍然增气”(亦详下引),则又对“简古”有所超越。
廖正一又擅四六。王铚《四六话》卷上曰:“廖友明略作四六,最为高奇。尝谓仆言:须要古人好语换却陈言,如职名二字便不可入四六。”他反对“陈言”,但又爱好“古人好语”,既不堆垛典故,又能汲收前人的语言精华,故所作“高奇”。
较之廖正一,李格非更以善论文知名当时。《宋史·李格非传》曰:
格非苦心于词章,陵轹直前,无难易可否,笔力不少滞。尝言:“文不可以苟作,诚不著焉,则不能工。且晋人能文者多矣,至刘伯伦《酒德颂》、陶渊明《归去来辞》,字字如肺肝出,遂高步晋人之上,其诚著也。
这段文字,当是檃括释惠洪语,《冷斋夜话》卷三曰:
李格非善论文章,尝曰:诸葛孔明《出师表》、刘伶《酒德颂》、陶渊明《归去来词》、李令伯《乞养亲表》,皆沛然从肺腑中流出,殊不见有斧凿痕。是数君子,在后汉之末,两晋之间,初未尝以文章名世,而其意超迈如此。吾以是知文章以气为主,气以诚为主。故老杜谓之诗史者,其大过人诚实耳,诚实著见,学者多不晓。
此论在宋代颇有名,《类说》卷五五、《仕学规范》卷三四等皆尝转录。李格非的意思是,作文一定要“诚”,才能使文章如“从肺腑中流出,殊不见有斧凿痕”。任何“诚不著”或伪饰情感的作品,都不可能有感人的力量,故“不能工”。若转换为现代文论话语,那就是“真实的感情是艺术的生命”。如此明确地提出求“诚”求真的美学主张,此前尚不多见。
李格非又以“横”论文。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六载其“杂书”二篇,其二论文章之“横”云:
余尝与赵遐叔言,孟子之言道,如项羽之用兵,直行曲施,逆见错出,皆当大败,而举世莫能当者,何其横也。左丘明之于辞令,亦甚横。自汉后千年,唯韩退之之于文,李太白之于诗,亦皆横者。近得眉山(指苏轼)《筼筜谷记》、《藏经记》,又今世横文章也。夫其横,乃其自得而离俗、绝畦径间者,故众人不得不疑。别人之行道文章,政恐人不疑耳。
他所谓的“横”,意思是有霸气,指文盖一世,他人所不可企及。与廖正一一样,李格非也崇尚《左传》,以左丘明为辞令“甚横”的作家。《墨庄漫录》卷六又记其杂书论左丘明、司马迁、班固、范晔、韩愈之才,他甚至将左丘明比作“绝代之女”,而司马迁只不过“如丽娼黠妇”,虽然偏颇,但也可见他对左氏的推崇。这在王安石和“王学”之徒鄙夷《春秋》、《左氏》学的时代,可谓矫枉过正,甚至是反其道而行之。那么文章如何才能“横”?他提出了三项原则:自得,离俗,绝畦径。若一言以蔽之,就是创新,以至为“众人”所难以接受而生“疑”,也在所不顾。没有创造性的作品便没有生命力,更不要说“横”了。
刘壎《隐居通议》卷六《评本之诗》载:
予尝于故箧断简中见有《诗评》者,曰:李文叔云:“出乎江西,则未免狂怪傲僻,而无隐括之妙;入乎江西,则又腐熟窃袭,而乏警拔之意。”……此说亦是用功于诗者而后能言之。
考昌彼得、王德毅等所编《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宋人李姓字“文叔”的,有李份、李格、李宗质、李格非四人。李份卒于元丰五年(1082)。黄庭坚是年三十八岁,知吉州太和县,诗名未著,诗坛也还没有所谓出入“江西”的情况。李格为绍兴时人,官终文林郎、知四会县,不以文名。李宗质卒于淳熙十一年(1184),累官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楼钥《朝散郎李公墓志铭》称其为“健吏”(21),精于理财,未言有文。则所谓“李文叔”,当非李格非莫属。在李格非时代,虽尚无“江西宗派”之目,但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人,赫然已为诗坛一大宗,而格非敏锐地觉察到江西诗人在“点铁成金”的旗号下“腐熟窃袭,而乏警拔之意”的弊端,不能不说是只眼独具。
“后四学士”的创作成就
当时知名文坛、同是苏轼友人的孔武仲,在《举自代》中写道:“宣德郎、秘阁校理、通判杭州廖正一,志操清洁,文学优深。向者玉堂对策,耸动众观。臣在馆阁,久与之处,见其所守,始终不移。”(22) 孔氏看重廖正一的,是“志操”和“文学”。前引叶梦得《廖明略竹林集序》,在论述了廖氏的文学主张后,进而评廖氏文章成就道:
明略自为举子时,即不沿袭场屋一语。再举而取进士,其所试,杰然已若可以名世者,至今为学者推重。盖其用志深苦,而思致精悫,渊源所从来者远矣。每一出语,辄有区域町畦,未有卒然而作者。至于出入经传,驱驾前言,左掐右摘,比次回曲,他人咀嚼梼杌终不能安者,明略绳约檃括,如以利刀摧朽木,尺箠呵群羊,无不如意。故其曲奥简洁,音节遒峻,精新焕发,使人读之,不觉矍然增气。惜其早困,不得尽用所长。始,元祐初,天下所推文章,黄、张、晁、秦号四学士,明略同直三馆,轩轾诸公间,无所贬屈,欲自成一家;然其流落不偶,略相似云。
惜乎现存廖正一作品太少,对叶氏的评说,已难以印证了。
廖正一的四六文,前引《四六话》卷上称“高奇”,同时举其佳句道:
明略《贺安厚卿启》曰:“远离门墙,遁迹江湖之外;闚望麾葆,荣光河洛之间。”又《贺张丞相启》云:“中台之光,下饰万物;前箸之画,外制四夷。进有德而朝廷尊,用真儒而天下服。”又云:“日月亭午,信无邪阴;山川出云,亟有时雨。”又谢厚卿答书之启云:“寂寞江滨,若戎车之陷淖;栖迟岩邑,信塞马之依风。暐然晨光,照此蔀屋。”
又谢伋《四六谈麈》也说:“廖明略正一,为四六甚工。旧见《为安厚卿举挂功德疏》云:‘梁木其摧,叹哲人之逝;天堂若有,须君子而登。生也有涯,没而不朽。痛两楹之梦奠,圮万里之长城。’其祭文云:‘昊天不惠,夺我元老。唐安得鉴,楚复观宝。盛德且然,小智宁保。’先公云:明略生平之学,熟于高氏小史。”(23) 从两家摘句看,廖氏四六很少堆垛典故,而善于熔铸或引用古语,如“远离门墙”(出韩愈《为河南令上留守郑相公启》“去离门墙”)、“梁木其摧”(出《礼记·檀弓上》)、“昊天不惠”(出《诗经·节南山》)等等,是他不用“陈言”而喜“古人好语”的绝佳实践,故能典雅新颖,“高奇”确为的评。
廖正一现存诗不多,以《和补之梅花》为出色:
蕙兰芳草久暌离,偶泄春光此一枝。自许轻盈羞粉白,何人闲丽得邻窥。寒欺薄酒魂宵夜,月入重帘梦破时。幸有暗香襟袖暖,江南归信不应迟。
此诗方回收入《瀛奎律髓》卷二○。在宋人众多的咏梅诗中,这也许不是最好的,但他不直接着笔于梅的物象,而刻画人的感受,从侧面点出梅品之高,颇得林和靖咏梅之妙,冯班尤称“腹联好”(24)。

李格非著《洛阳名园记》
李格非是北宋文章名家。《涧泉日记》卷下曰:“巩丰仲至言尹少稷称李格非之文,自太史公之后,一人而已。”因李格非的文章流传至今的不多,尹氏所论是否得当,已难评判,就算誉之稍过,至少宋人有此一说。《后村诗话》续集卷三曰:“文叔《祭淇水(李清臣)文》云:‘惟先生自《诗》《书》以来载籍所记,历代治乱,九流百氏,凡一过目,确不忘坠。其发为文章,则泛而汪洋,密而精致,翛然高爽,敛然沉毅,骤肆而隐,忽纷而治,绝驰者无遗影,适淡者有余味,如金玉之就雕章,湖海之失涯涘,云烟之变化,春物之秾丽,见之者不能定名,学之者不能仿佛。’笔势略与淇水相颉颃,□□□□□,精深可讽味。”李清臣得到过欧阳修的赏识,尝比之于苏轼,(25) 而《祭淇水文》滔滔汩汩,大有苏文气象,不难看出欧、苏文风递传的脉络。
在李格非现存不多的作品中,《破墨癖说》可谓杰作。(26) 这是一篇小品文,写“客”以贮墨为癖,“其制为璧、为丸、为手握,凡十余种,一一以锦囊之”,而以出于历代制墨名家李廷珪、李承宴、张遇相炫耀。作者对此颇不以为然:“既而私怪予用薛安、潘谷墨三十余年,皆如吾意,不觉少有不足,不知所谓廷珪墨者,用之当如何也。”于是引出下面一段对话:
他日,客又出墨。余又请,其说甚辩。余曰:“嘘,余可以不爱墨矣。且子之言曰:‘吾墨坚,可以割。’然余割当以刀,不以墨也。”曰:“吾墨可以置水中,两宿不腐。”然吾贮水以盆罃,不用墨也。客复曰:“余说未尽。凡世之墨,不过二十年,胶败,辄不可用。今吾墨皆百余年不败。”余曰:“此尤不足贵。余墨当用二三年者,何苦用百年墨哉!”
于是“客辞穷”,但“心欲取胜”,“曰:‘吾墨黑。’余曰:‘天下固未有白墨。虽然,使其诚过他墨,犹足尚。’乃使取砚,屏人,杂错以他墨书之,使客自辨,客亦不能辨也。”收墨成癖,但杂错以他墨书之,却“不能辨”,已十分可笑。接着,作者发了如下一段议论:
今墨之用在书,苟有用于书,与凡墨无异,则亦凡墨而已焉,乌在所宝哉!嗟乎,非徒墨也,世之人不考其日用而眩于虚名者多矣,此天下寒弱祸败之所由召也,吾安可以不辨于墨!
至此,作者从“破墨癖”这件小事,引出一个发人深省的大道理:到底是讲实用,还是图虚名?最后再进一层,将图虚名的危害提到“天下寒弱祸败之所由”的高度,以小见大,发人深省。全文不过五百来字,立论高超,文字生动流畅。尝鼎一脔,李格非的文学创作成就,由此可窥一斑。
朱熹曾说:“李文叔,前此亦但见其论文数篇,颇有可观,今亦不能记忆,但如《战国策序》,则恐文健意弱,太作为伤正气耳。”(27) 朱熹以为《战国策序》“太作”,但对李格非的文章,还是赞许的。王士祯曰:“吾郡李文叔格非,元祐君子也。其集不传,传者仅《洛阳名园记》一卷,可略见其梗概。此外遗文数篇,杂见说部,余已录之。近从《枫窗小牍》又得元祐六年七月哲宗幸太学,宰执侍从吕大防、苏颂、韩忠彦、苏辙、冯京、王岩叟、范百禄、梁焘、刘奉世、范纯礼、孔武仲、顾临等三十六人纪事唱和诗序一碑,雅洁,是元祐作者风气。”(28) 要之,李格非的散文、四六,在元祐文学群体中颇为杰出,刘克庄甚至认为在晁(补之)、秦(观)之上(见下引)。
李格非也是有名的诗人。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卷三曰:
李格非……文高雅条鬯,有义味,在晁、秦之上,诗稍不逮。元祐末为博士,绍圣始为礼部郎,有《挽蔡相确》诗云:“邴吉勋劳犹未报,卫公精爽仅能归。”岂蔡尝汲引之乎?《挽鲁直》五言八句,首云:“鲁直今已矣,平生作小诗。”下六句亦无褒词。文叔与苏门诸人尤厚,其殁也,文潜志其墓。独于山谷在日,以诗往还,而此词如此,良不可晓。其《过临淄》绝句云:“击鼓吹竽七百年,临淄城阙尚依然。如今只有耕耘者,曾得当时九府钱。”《试院》五言云:“斗暄成小疾,亦稍败吾勤。定是朱衣吏,乘时欲舞文。”亦佳作。……《初至象郡》五言云:“裨海环□□,□□□□国。世人持两足,遽欲穷畛域。心知禹分土,未尽舜所陟。吾迁桂岭外,仰亦见斗极。升高临大路,邮传数南北。山川来时经,草树略已识。枝床归梦长,乡堠行历历。”……(以下犹录诗四首,此略)
挽黄庭坚而无褒词,甚至说“平生作小诗”,是否如前《隐居通议》引《诗评》所载,流露了他对江西诗风的不满?尚待研究。王士祯亦称其《临淄怀古》绝句(即《过临淄》)“颇可诵”(29)。
李格非著作完整保存至今的,是作于绍圣二年(1095)的《洛阳名园记》,其时为校书郎。此书记洛阳名园十九所,规模很小,其实就是一篇“记”。他在《书洛阳名园记后》(30) 中说:“园囿之兴废,洛阳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乱,候乎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候乎园囿之兴废而得。则《名园记》之作,余岂徒然哉!呜呼,公卿大夫方进于朝,放乎以一己之私自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乐,得乎?唐之末路是也。”李格非目睹上层统治集团腐败营私而表现出的强烈的忧患意识,是他写作此书的目的。张琰《洛阳名园记序》曰:
山东李文叔记洛阳名园,凡十有九处……观文叔之记,可以知近世之盛,又可以信文叔之言为不苟。且夫识明智审,则处事精而通道笃,随其所见浅深为近远小大之应。于熙宁变更,天下风靡,有所谓必不可者,大丞相司马公为首,后十五年无一不如公料者。至今明验大效,与始言若合符节。文叔方洛阳盛时,脚迹目力心思所及,亦远见高览,知今日之祸,曰:“洛阳可以为天下治乱之候。”又曰:“公卿高进于朝,放乎一己之私意,忘天下之治忽。”呜呼!可谓知言哉!文叔在元祐官太学。丁建中靖国再用邪朋,窜为党人。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四也说:“予得李格非文叔《洛阳名园记》,读之至流涕。文叔出东坡之门,其文亦可观,如论‘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囿之兴废。’其知言哉!”《名园记》所记,乃全盛时洛阳风景,“靖康之难”后,洛阳沦于金,故此书最能引起时人的今昔之感,极大地刺激着南宋人痛苦的神经。如《崇古文诀》卷三二评李格非《书洛阳名园记后》时所说:“园囿何关于世道轻重,所以然者,兴废可以占盛衰,可以占治乱。盛衰不过洛阳,而治乱关于天下。斯文之作,为洛阳,非为园囿;为天下,非为洛阳。文字不过二百字,而其中该括无限盛衰治乱之变,意有含蓄,事存鉴戒,读之令人感叹。”李格非超前的忧患意识和卓越的政治远见,不能不令人佩服。
李格非还著有《历下水记》。《墨庄漫录》卷四曰:“济南为郡,在历山之阴,水泉清冷,凡三十余所,如舜泉、爆流、金线、真珠、洗钵、孝感、玉环之类,皆奇。李格非文叔为《历下水记》,叙述甚详,文体有法。曾子固作诗,以爆流为趵突,未知孰是。”则该书记济南名泉。“爆流”当即趵突泉的别称。王士祯曰:“按文叔《水记》,宋人称之者不一,而不得与《洛阳名园记》并传,可恨也。吾郡名泉凡七十二,此云三十余者,盖未详也。”(31)
李禧、董荣存世作品太少,已无可论,但从前引李禧题画诗和董荣残词看,他们的文学修养亦不俗。
综上所述,韩淲《涧泉日记》称廖正一等四人当日号“后四学士”,当得其实。“后四学士”中的廖正一、李格非,元祐间曾受知苏轼,李禧、董荣盖也有大略相似的经历,而廖、李又先后入党籍,政治上与苏轼及黄庭坚等“四学士”的遭遇相同。虽限于史料,对他们的生平事迹、他们与苏轼的关系,以及四人间的相互关系等皆知之不多(李、董几无所考),而四人文集又都亡佚,很难窥其创作全貌;但从流传篇什和宋人评说中,可知他们的文学理论和诗文创作都颇具特色,与前“四学士”一样,他们也是苏轼文学的传人,元祐文坛的中坚。固然,就整体成就和在文学史上的影响论,“后四学士”盖难与前“四学士”比肩;但当日既有此称,其群体应足以不让黄、秦、晁、张专美于前。发掘和研究“后四学士”,无论对研究元祐文学,还是对全面考察苏轼文学集团,都具有开拓疆域、扩大视野、丰富内涵的意义。